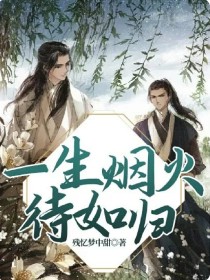第三十一章 圆满
仔细想想,似乎他们的结局都不圆满,甚至算不得好。曾祖父幼年贫困,中年丧命。
而曾祖母为了所爱之人与父母断绝关系,却仍是不得善终。早年丧夫,晚年“丧”子,辛苦一辈子,最后只落得含恨惨死。
母亲出身书香名门,受尽万千宠爱,却是自幼体弱多病。尚不至中年,便已…
我抹了眼泪,重新奉上三柱香,叩拜完,回了母亲生前的住处——菡萏院。
安疏安青自母亲去世后,便自请去了阐灵庙修行,为母亲和褚家祈福。
母亲房中的陈设一如从前她还在的时候,一年来未有过一丝的变动。所有器具上的图纹,仍是她最爱的菡萏花。
我的手拂过桌面,手指上没沾半点灰尘。房间干净的一尘不染,像是每日都有被人打扫。
走到母亲生前常坐的罗汉床边,我抱起上面的软枕,将头轻轻的靠在上面,眼帘微阖。
忽然想起我十三岁那年,母亲曾有一段时间突然迷恋上了看戏。都城内有名的戏楼不在少数,但母亲只去讼雅楼,还总是看同一个人演的戏。
倒不是我疑心,而是母亲并没有瞒我。她同我说,她看的那位先生,曾是她的故人。
先生名叫苏何,听说并非是大昌子民,但无人知他从何而来,亦不知其姓名是真是假。但他极爱扮戏,到了痴狂的地步。十四岁到讼雅楼,不到一年,他的戏便传遍了大江南北,被文人骚客所称赞。
我曾随母亲去看,但他的戏极为深奥,如我这般俗人,实难了了。
我问母亲,“先生的戏奇辞奥旨,常人难以看懂,并不有趣,阿娘为何喜欢看?”
她说,“我看的不止是戏。”
我说:“灵均不懂。”
阿娘又说:“不懂才是最好的。若是可以,阿娘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懂。”
她每次看向戏台,或者是扮戏的人,眼中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我从来不曾看懂。
她说苏何先生是她的故人。我想,应是未遇见我阿爹以前他们就已经相识了吧。
但未等到我看懂的时候,苏何先生却突然离开了都城,此后再未出现。无人知晓他去了哪里。
我不知,阿娘也不知。
他们从未说过话,一个只扮戏,一个只看戏,自始至终都未有过半点交涉,但我知道,自从苏何先生离开都城之后,阿娘就再没去过讼雅楼。
或许她的遗憾不是感叹自己命薄,而是她那埋藏在心底不曾拥有也不曾失去过的…或许可以说成是一种名为“情感”的东西吧。
我不知自己何时睡着的,但醒来时身上多了一层薄毯。
父亲坐在梨花桌旁,眼睛盯着桌面,一动不动,似乎也在回忆过往。
此时的他卸去了平日里的威严,不像是一名驰骋沙场,身经百战的将军,只像一个普通人家的丈夫和父亲。
他为什么在这?
不必问。
我知道,他也在思念着阿娘。他深深地爱着阿娘。
我从床上坐起,轻声唤道:“阿爹。”
他回过神,眸中满是复杂,看到我,他脸上露出一抹牵强的笑,“这么大的人了,睡觉也不知道盖被子。你阿娘日后不能再给你盖了,阿爹也不能随时照看着你,所以长安要记得,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我鼻尖一酸,却仍是扬起一张笑脸,撒娇似的说道:“有阿爹在,长安可以只是不会照顾自己囡囡。”
儿时总想快些长大,因为长大后就不用受阿娘管教。可终于等到真的长大了,却又想回到儿时,那般无忧无虑。
所有亲人都在。
又过了月余,安疏派人传来一则消息,说是祖母过世。
她在信中并阐明,祖母是因何故亡。
父亲自去阐灵庙接回祖母,才得知祖母是自己在房中点了火…
父亲难过了许久,祖父听闻这个噩耗时,曾看惯了血流成河,伏尸千里的样子。战神如他,竟也止不住地也落下泪来。
安疏在信上说,祖母在自己的袇房外放置了一封遗书。
她说,当我们看到这封信时,她已经葬身火海。她希望在她身死后,父亲能把她的骨灰撒到莫南山山顶。她生前被困了一辈子,死后想自由些。
她还说,希望父亲把她的名字从褚家族谱上除名。她说她倦了,想自己的阿爹阿娘,想回到东陵,不想再做褚家的人了。
她全书从头至尾,未曾提及关于祖父的一字半句。
她自韶华之年起,嫁与祖父半生。到头来,临死了希望的是自己的儿子替自己料理后事,也不愿留只言片语给自己的丈夫。
那段时间,祖父的身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疾速消瘦。
父亲遵照祖母的遗愿,将她的骨灰撒到了莫南山的山顶。
微风掠过东陵,掠过莫南山山上的每一棵树木和花草,连同带着祖母一起去了远方。
是她所向往的自由。
桃华梦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同创文学网http://www.tcwxx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相关小说
- 雪精灵:奶萌公主棒棒哒
- 简介:雪精灵在边塞遇到了一位小女孩,为了帮她实现愿望,自己变成了夏国公主,在回到夏国之后,皇帝爹爹连同他的哥哥一起宠她。简直要啥有啥。只不过雪精灵可是一个职业派,要努力的实现小女孩的愿望,让她的名字流传千古,为此,雪精灵可是做了好多功课呢。“爹地爹地,要致富,先修路。快把水泥的制作方法拿去。”“爹地爹地,军火够不够用啊?我这还有好多。”雪精灵拿出了轰击大炮98k。“爹地爹地,冰块为什么这么贵啊?贵的话,我这还有好多。”雪精灵一挥手,一堆冰就出现在了地上。“爹地爹地……”雪精灵又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啦。皇帝爹地表示无奈,自己女儿就是这么优秀。别的国家皇帝争着要把自己女儿抢走。雪精灵的哥哥们猛的一扭头。“想抢妹妹?”大哥哥跑到你家抄你九族。二哥哥跑到你家拆家,速度堪比十只哈士奇。三哥哥在你夜里回家时套麻袋蒙头就是一顿揍。用不了多久,你就会倾家荡产,连下床都不能自理。为此,雪精灵表示无奈。怎么办好呢?我的哥哥就是这么宠我。只不过,四哥哥怎么有些奇怪?他的眼神好想吃了我呀。(敌国太子乔装打扮的四哥哥vs呆萌可爱的雪精灵)超甜Ⅹ超爽X超爆
- 1.0万字2年前
- 春华绝代
- 简介:成长记~
- 3.0万字2年前
- 一生烟火待如归
- 简介:在这暗流涌动的朝堂上,我愿点一盏灯,静待如归;愿管他凡事清浊,为你一间轮回甘坠。庆朝的风云中,韩懿(长泽)与陈昶(如归)一同如破竹,携手用一生的烟火,只为换彼此一瞬的停留,去吻别苦楚,吻别沧桑年华。前许有父母,后许有彼此,一切安好!彼岸花花海虽艳,我不喜,只因他花叶生生相错!世间纵有许多倾城容貌,我不喜,只因我心中已有盛世佳颜,无心力,也不愿再去他赏。韩懿在别人眼中是权势滔天的大佞臣,原因只是为了他心中不喜朝堂尔虞我诈的那个人,能在这本是囚笼的地方,多一些喜笑,多一份护航。
- 3.9万字2年前
- 傲娇王爷顽皮妃
- 简介:我不想写
- 0.1万字2年前
- 王爷驾到:王妃别想逃
- 简介:江虞国将军府里林笑笑作为将军府的小透明,她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米虫,可是生活永远不会让她顺心,姨娘和庶姐设计让她嫁给了鬼云王爷。鬼云王爷是江虞国的三王爷江亦然,生来冷血无情,杀人如麻。是江虞国人人避之。且看林笑笑和江亦然之间的故事吧!
- 0.8万字2年前
- 有药改编
- 简介:懒
- 0.1万字2年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