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3з« зғ«жүӢеұұиҠӢ
ж”Ҝж№ғеҗҺи„ҠжўҒдёҖйҳөеҸ‘еҮүпјҢд»–еқҗиө·иә«пјҢдҫ§иҖід»”з»Ҷеҗ¬пјҢйҷӨдәҶжЈҡеӨ–зҡ„йЈҺеЈ°пјҢе’ҢеҒ¶жңүзҡ„еҮ еЈ°йёҹйёЈпјҢеұӢйҮҢеҫҲйқҷгҖӮд»–и¶ҝжӢүдёҠйһӢеңЁеұӢйҮҢеұӢеӨ–иҪ¬дәҶдёӨеңҲпјҢиҝҳжҳҜжІЎжңүеҠЁйқҷгҖӮ
ж”Ҝж№ғеҝғжғіпјҡвҖңйҡҫдёҚжҲҗжҳҜиҖҒйј пјҹе“ӘжҖ•жңүеҸӘиҖ—еӯҗйӮЈд№ҹжҳҜеҗғзҡ„е•Ҡ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қҗеҲ°иҚүеёӯдёҠеҲҡиҰҒиәәдёӢпјҢдёҖеЈ°е’•еҷңе’•еҷңйёЈеҸ«еЈ°жё…жҷ°ең°дј жқҘпјҢиҝҷж¬Ўд»–еҗ¬жё…дәҶпјҢеЈ°йҹіжҳҜд»Һйҷ¶з“®йҮҢеҸ‘еҮәжқҘзҡ„гҖӮ
ж”Ҝж№ғзӮ№дёҠзҒҜпјҢеӣҙзқҖйҷ¶з“®иҪ¬дәҶдёҖеңҲпјҢд»”з»ҶжҹҘзңӢдёҖз•ӘеҗҺеҝғйҮҢеӨ§е–ңпјҡвҖңиҝҷйҷ¶з“®дёҠжңүе°Ҹеӯ”пјҢеҰӮжһңжҳҜзҺүзұіз§ҚеӯҗпјҢж—©е°ұеҫҖеӨ–жҺүзҺүзұізІ’е„ҝдәҶпјҢйҡҫдёҚжҲҗиҝҷйҮҢжңүжқЎзӢ—пјҹзӢ—иӮүеҸҜжҜ”иҖ—еӯҗиӮүйҰҷзҷҫеҖҚе•Ҡ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蹑жүӢ蹑и„ҡиө°еҲ°еұӢеӨ–пјҢжҚЎдәҶдёҖеқ—зҹіеӨҙпјҢеҮ‘еҲ°йҷ¶з“®еүҚпјҢеҳҙйҮҢеӯҰзқҖзӢ—еҸ«пјҡвҖңжұӘпјҢжұӘжұӘвҖҰвҖҰвҖқ
еӣһзӯ”д»–зҡ„пјҢжҳҜдёҖеЈ°жӮ й•ҝзҡ„иӮҡеӯҗйёЈеҸ«з”ҹгҖӮ
ж”Ҝж№ғжҜ«дёҚзҠ№иұ«ең°жҠҠзҹіеӨҙз ёеҲ°дәҶйҷ¶з“®зҡ„еӨ§иӮҡеӯҗдёҠпјҢдёҖеЈ°жІүй—·зҡ„з“ҰзүҮзўҺиЈӮеЈ°еҗҺпјҢйҷ¶з“®еҸӘиў«еҮҝ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иЈӮзә№пјҢж”Ҝж№ғеӨ§жҖ’пјҡвҖңиҖҒеӯҗдёҚеҸ‘зҒ«пјҢдҪ иҝҳзңҹдёҚзҹҘйҒ“дҪ дәҢеӨ§зҲ·жҳҜдёӘзҲ·д»¬гҖӮвҖқ
д»–жҠЎиө·зҹіеӨҙпјҢе“җе“җзҢӣз ёпјҢйҷ¶з“®иҮӘдёҠиҖҢдёӢзўҺжҲҗдәҶдёүз“ЈпјҢж”Ҝж№ғеҚҙеҗ“еҫ—иҝһиҝһеҗҺйҖҖгҖӮ
йҷ¶з“®йҮҢз«ҹ然жҳҜдёҖдёӘиң·зқҖиә«еӯҗзҡ„еҰҷйҫ„еҘіеӯҗгҖӮ姑еЁҳдёҠиә«з©ҝ зӣҳиқҙиқ¶з»“жүЈе„ҝ з»ЈиҠұйӣӘзҷҪе°Ҹиў„пјҢеӨ–еҘ—дәҶжқҸй»„дёқз»өеқҺиӮ©пјҢдёӢеӨҙз©ҝзҷҫиӨ¶иЈҷеӯҗеҚҙд№ҹжҳҜзұізҷҪиүІпјҢеӨҙдёҠзҸ з»“зҝ з»•пјҢеҲҳжө·еҰӮдёҖжҚ§йқ’зғҹпјҢж•°зӣ®дјјжңҰиғ§еҶ°йӣҫгҖӮ
еӣ дёәеңЁзҝҒдёӯж—¶й—ҙеӨӘй•ҝдәҶпјҢиҝҷ姑еЁҳи…ҝи„ҡйғҪйә»дәҶпјҢзҺ°еңЁиә«еӯҗд№ҹдјёеұ•дёҚејҖпјҢеҘ№еҶ·зңјзӣҜзқҖж”Ҝж№ғгҖӮ
ж”Ҝж№ғе‘ҶиӢҘжңЁйёЎпјҢж„ЈзҘһеҚҠеӨ©жүҚй—®пјҡвҖңдҪ вҖҰвҖҰдҪ жҳҜйӮЈиҖҒеӨӘеӨӘзҡ„е„ҝеӘіеҰҮпјҢеҜ№еҗ§пјҹвҖқ
еҘіеӯҗжүӯжүӯжүӢи…•гҖҒжҙ»еҠЁжҙ»еҠЁиӮ©иҶҖпјҢй”ӨдәҶй”ӨеӨ§и…ҝпјҢжҷғдәҶжҷғи„ҡпјҢз«ҷиө·иә«зңӢдәҶзңӢеұӢйҮҢзҡ„еёғеұҖпјҢи„ёдёҠжІЎжңүд»»дҪ•иЎЁжғ…пјҢд№ҹжІЎеӣһзӯ”ж”Ҝж№ғзҡ„иҜқгҖӮ
ж”Ҝж№ғи®ЁдәҶдёҖдёӘж— и¶ЈпјҢиҮӘиЁҖиҮӘиҜӯйҒ“пјҡвҖңжҖӘдёҚеҫ—иҖҒеӨӘеӨӘи·ҹз–ҜдәҶдјјзҡ„жӢҺзқҖиҸңеҲҖиҝҪжҲ‘е‘ўпјҢеҘ№жҖҺд№ҲдёҚж—©иҜҙе‘ўпјҢжҲ‘иҙ№еҠІеҗ§е•Ұзҡ„жүӣзқҖдёҖдёӘе°‘еҰҮжјӮжҙӢиҝҮжө·зҡ„пјҢе®№жҳ“еҗ—пјҹеҸҲдёҚиғҪеҗғеҸҲдёҚиғҪвҖҰвҖҰвҖқ
жӯЈеҳҖе’•зқҖпјҢж”Ҝж№ғеҝҪ然жғіиө·д»Җд№ҲпјҢд»–д»”з»ҶзңӢдәҶзңӢйқўеүҚиҝҷ姑еЁҳпјҢ姑еЁҳеӨҙйЎ¶дёҠж–№жҳҫзӨәзҡ„ж•°еӯ—жҳҜ1.дёҚиҝҮпјҢиҝҷдёӘ1еҫҲеҘҮжҖӘпјҢжҳҜз»ҜзәўиүІзҡ„пјҢеҫҲеҫҲйІңиүіпјҢд№ҹеҫҲжҳҫзңјгҖӮ
ж”Ҝж№ғеҝғдёӯжҡ—жғіпјҡвҖңеҺҹжқҘзҝ еұҸеұұйӮЈиҫ№зҡ„дәәж•°зӣ®еӯ—жҳҜеҪ©иүІзҡ„пјҢе”үпјҢ1еЎ”еёғпјҢиғҪе№ІзӮ№д»Җд№Ҳе‘Җ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жҸҗй«ҳеЈ°и°ғпјҢеҸҲй—®пјҡвҖңдҪ жҳҜдёҚжҳҜйӮЈиҖҒеӨӘеӨӘзҡ„е„ҝеӘіеҰҮпјҹиҝҳжҳҜеҘ№й—әеҘіе•ҠпјҹвҖқ
еҘіеӯҗдёҚеҶ·дёҚзғӯзҡ„еӣһзӯ”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жҳҜ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ж°”зҡ„пјҢиҝҷдё«еӨҙи„‘еӯҗиҝӣж°ҙдәҶеҗ§пјҢеҲ°еә•жҳҜе„ҝеӘіеҰҮиҝҳжҳҜй—әеҘіе•ҠгҖӮ
姑еЁҳжҠҠиә«дёҠйӮЈдәӣйҷ¶з“®зҡ„зўҺзүҮзўҺжёЈзўҺжң«жҺёиҗҪпјҢеӨ§д№үеҮҢ然ең°й—®йҒ“пјҡвҖңдҪ жғіжҠҠжҲ‘жҖҺд№Ҳж ·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ҮҠжҒјзҡ„жҖјдәҶеӣһеҺ»пјҡвҖң姑еҘ¶еҘ¶пјҢжҲ‘иғҪжҠҠдҪ жҖҺд№Ҳж ·е•ҠпјҹжІЎжі•еҗғдәҶдҪ пјҢдҪ иә«дёҠеЎ”еёғиҝҳиҝҷд№ҲжҳҫзңјпјҢжҲ‘еҸӘиғҪжҳҜиҮӘи®ӨеҖ’йңүдәҶгҖӮвҖқ
姑еЁҳдёҖж„ЈпјҡвҖңдҪ пјҢдҪ д»Җд№Ҳж„ҸжҖқ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ҢҮдәҶжҢҮй—ЁпјҡвҖңдҪ иө°еҗ§пјҢд»ҺеӨ–иҫ№жҠҠй—Ёз»ҷжҲ‘еёҰдёҠпјҢжҲ‘еҸҲйҘҝеҸҲзҙҜпјҢзҺ°еңЁе°ұжғізқЎдјҡе„ҝгҖӮвҖқ
姑еЁҳзңӢдәҶзңӢжјҸйЈҺзҡ„еұӢй—ЁпјҢеҸҲзһ§дәҶзһ§ж”Ҝж№ғпјҡвҖңдҪ вҖҰвҖҰдҪ е’ҢеҲ«дәәжҖҺд№ҲдёҚдёҖж ·е‘ў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иҮӘе°Ҡеҝғиў«дјӨе®ідәҶпјҢиҜҙиҜқе°ұжңүзӮ№иө°дёӢеқЎи·ҜдәҶпјҡвҖңиҖҒеӯҗд»ҘеүҚд№ҹжҳҜжңүй’ұдәәпјҢзҺ°еңЁиҗҪйӯ„дәҶпјҒиӮүеҲҶдә”иҠұдёүеұӮпјҢдәәеҲҶдёүе…ӯд№қзӯүпјҢжңЁжңүиҠұжўЁзҙ«жӘҖпјҢжңҲжңүйҳҙжҷҙеңҶзјәпјҢжӯӨдәӢеҸӨйҡҫе…ЁпјҢдҪҶж„ҝдәәй•ҝд№…пјҢдәәж°‘иӢұйӣ„пјҢж°ёеһӮдёҚжңҪпјҒдҪ з»ҷжҲ‘иө¶зҙ§иө°пјҢиҜҙиө°дҪ е°ұиө°пјҢйЈҺйЈҺзҒ«зҒ«й—Ҝд№қе·һпјҒжҲ‘иҝҷеӣһзӯ”пјҢдҪ ж»Ўж„ҸдәҶеҗ—пјҹвҖқ
姑еЁҳеҗ¬еҫ—жңүдәӣжҮөпјҢдҪҶеҶ·еҶ·и§ЈйҮҠ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жҲ‘дёҚжҳҜиҜҙдҪ з©·гҖӮжҲ‘жҳҜиҜҙпјҢдҪ иҝҷдәәе’Ңжӣҝд»–дәәдёҚдёҖж ·пјҢдҪ еҝғе–„гҖӮеңЁзҷҪйқ’е ЎпјҢдҪ дёҚдҪҶжІЎжңүжқҖдәәпјҢиҝҳж•‘дәҶе©Ҷе©Ҷ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Ӯ№еӨҙпјҡвҖңеҜ№е‘ҖпјҢдҪ зңӢпјҢжҲ‘еҝғе–„иҗҪдәҶдёӘд»Җд№ҲдёӢеңәпјҢжң¬жқҘжғіжүӣеӣһжқҘдёҖзјёзӣҗпјҢжҺҘиҝҮжҗ¬еӣһжқҘдҪ иҝҷд№ҲдёҖдёӘвҖҰвҖҰе“ҺпјҢеҜ№дәҶпјҢдҪ еҸ«д»Җд№ҲеҗҚеӯ—пјҹвҖқ
姑еЁҳиӯҰи§үең°й—®пјҡвҖңе№Іеҳӣ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й—®жҲ‘зҡ„еҗҚеӯ—пјҢдҪ жғіе№Ід»Җд№Ҳ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ҒЁеҫ—зүҷж №з—’з—’пјҡвҖңдҪ дјҡе” е—‘еҗ—пјҹдҪ дјҡиҜҙдәәиҜқеҗ—пјҹжҲ‘иғҪеӣҫдҪ д»Җд№Ҳе‘ҖпјҢжҲ‘еӣҫдҪ зҡ„иҙўпјҹдҪ иә«дёҠжүҚ1еЎ”еёғпјҢиҖҒеӯҗеңЁзӣ‘зӢұйҮҢз»ҷйӮЈдёӘжҹіе§‘еЁҳжү“иөҸеҮәжүӢе°ұжҳҜдёҖеЎ”еёғгҖӮжҲ‘еӣҫдҪ зҡ„иүІпјҹиҖҒеӯҗзҺ°еңЁйҘҝзҡ„йғҪжҢӘдёҚеҠЁзӘқдәҶпјҢжңүйӮЈдёӘеҝғд№ҹжІЎдёӘеҠІе„ҝгҖӮеҺ»еҗ§пјҢеӣһ家еҺ»еҗ§гҖӮвҖқ
иҝҷ姑еЁҳеҸ‘зҺ°пјҢеҜ№йқўзҡ„ж”Ҝж№ғиҜҙиҜқиҷҪ然жҳҜйў дёүеҖ’еӣӣпјҢеҸҜеҘҪеғҸзЎ®е®һжІЎжңүжҒ¶ж„ҸгҖӮеҘ№иҝҳжҳҜдёҚеӨӘж”ҫеҝғпјҢеӣ дёәпјҢиҮӘе°ҸеҲ°еӨ§пјҢеӯӨйӣ¶еІӣдёҠиҝҷзҫӨдәәпјҢиҝҷжүҖжңүдәәзҡ„еҳҙи„ёпјҢеҘ№еҗ¬д№ҹеҗ¬и…»дәҶпјҢзңӢд№ҹзңӢи…»дәҶпјҢйғҪжҳҜе”ҜеҲ©жҳҜеӣҫзҡ„дәәжёЈгҖӮеҘ№д»Һең°дёҠжҚЎиө·дәҶдёҖеқ—зҹіеӨҙпјҢеҒҮиЈ…иө·иә«пјҢиҜ•жҺўең°иҜҙйҒ“пјҡпјҢвҖңйӮЈжҲ‘е°ұе‘ҠиҫһдәҶ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еӣһйҒ“пјҡвҖңдё”ж…ўпјҒвҖқ
姑еЁҳиӯҰи§үең°ж”Ҙзҙ§дәҶзҹіеӨҙпјҢеҚҙеҗ¬ж”Ҝж№ғ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дҪ жҠҠзҒҜз»ҷжҲ‘еҗ№дәҶпјҢжҠҠй—Ёд»ҺеӨ–иҫ№з»ҷжҲ‘еёҰдёҠпјҢжҲ‘е°ұдёҚиө·жқҘдәҶпјҢжөӘиҙ№жҲ‘иә«дёҠзҡ„еҚЎи·ҜйҮҢгҖӮвҖқ
姑еЁҳеҖ’йҖҖзқҖеҫҖеӨ–иө°пјҢж”Ҝж№ғиәәеңЁиҚүеёӯдёҠпјҢжүӯиҝҮи„ёпјҢеҝғйҮҢжғізҡ„жҳҜпјҡвҖңжҲ‘иҝҳжғізқҖжЈ’еӯҗйқўиҙҙйҘјеӯҗе‘ўпјҢзҺ°еңЁиҝһзҺүзұіз§ҚеӯҗйғҪдёҚжҳҜпјҢжҳҺеӨ©еҗғд»Җд№Ҳе‘ҖпјҢйҡҫйҒ“жҲ‘д№ҹи·ҹиҖҒзҷҪдёҖеқ—еҺ»дјҗжңЁпјҹвҖқ
з“®дёӯиҖҢеҮәзҡ„姑еЁҳеҗ№зҒӯдәҶзҒҜпјҢеҖ’йҖҖзқҖеҮәдәҶй—ЁпјҢеңЁеӨ–иҫ№з«ҷдәҶдёҖдјҡе„ҝпјҢдҫ§иҖідёҖеҗ¬пјҢеұӢйҮҢдёҖзӮ№еҠЁйқҷйғҪжІЎжңүгҖӮ
еҘ№иў«з§ӢйЈҺдёҖеҗ№пјҢи„‘еӯҗжё…йҶ’дәҶеҫҲеӨҡпјҢиҮӘе·ұжғіиҰҒеӣһеҺ»пјҹи°ҲдҪ•е®№жҳ“е•ҠпјҢеӯӨйӣ¶еІӣеӣӣйқўзҺҜж°ҙпјҢе’Ңзҝ еұҸеұұйҡ”зқҖиҢ«иҢ«еӨ§ж№–пјҢдёҖеӨ©дёҖеӨңжүҚиғҪеҲ°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иҮӘе·ұеӨҙйЎ¶зқҖеҪ©иүІзҡ„еЎ”еёғпјҢиў«еҲ«дәәзңӢеҲ°пјҢз«ӢеҚіе°ұжҳҜеҸ—иҫұиҖҢжӯ»гҖӮ
жғіеҲ°иҝҷе„ҝпјҢеҘ№и№ІеқҗеңЁжЈҡжӘҗдёӢпјҢиЈ№зҙ§дәҶиЎЈжңҚпјҢиҢ«з„¶иҖҢ委еұҲзҡ„еҸҢжүӢжүҳи…®пјҢжҖқжқҘжғіеҺ»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еҠһжі•гҖӮиӮҡеӯҗйҮҢдёҚеҒңең°е’•е’•еҸ«зқҖжҠ—и®®гҖӮеҘ№дёҖзӢ еҝғпјҢжҺЁй—ЁпјҢеҸҲеӣһеҲ°дәҶеұӢеҶ…гҖӮ
еӣһпјҢеҸҜжҳҜеӣһжқҘдәҶпјҢиҖҢдёӢдёҖжӯҘжҖҺд№ҲиҜҙпјҢжҖҺд№ҲеҒҡе‘ўпјҹ
еӣ дёәж”Ҝж№ғеӨӘзҙҜдәҶпјҢе·Із»ҸзқЎзқҖдәҶпјҢе°Ҹе‘јеҷңжү“зҡ„еҖҚе„ҝеқҮеҢҖпјҢеҘ№иҷҪ然дёҚзҹҘйҒ“дёәд»Җд№ҲиҝҷдёӘз”·еӯҗз«ҹ然ж”ҫиҝҮиҮӘе·ұпјҢдҪҶеҘ№еҚҙиғҪзңӢеҫ—еҮәпјҢйқўеүҚиҝҷе°ҸдјҷпјҢеҜ№иҮӘе·ұж— жүҖеӣҫпјҢиө·з ҒжҳҜжІЎжңүжҒ¶ж„ҸгҖӮ
иҮӘе·ұзҺ°еңЁжҖҺд№ҲеҠһпјҹеқҗпјҹеқҗеңЁе“ӘпјҹиәәпјҹйҡҫдёҚжҲҗиәәеңЁз”·еӯҗиә«иҫ№пјҹжғіеҲ°иҝҷе„ҝ姑еЁҳйғҪдёҖзүҮи„ёзәўгҖӮ
еҘ№иөҢж°”дјјзҡ„з”ЁжүӢдёӯзҹіеӨҙз ёеҗ‘з ҙзҝҒпјҢеҳЎе•·дёҖеЈ°е“ҚпјҢеҗ“еҫ—ж”Ҝж№ғдёҖе“Ҷе—ҰпјҢж”Ҝж№ғеңЁй»‘жҡ—дёӯжҸүзқҖзңјпјҢзһ§и§ҒдәҶдёҖдёӘеЁҮе°Ҹзҡ„иә«еҪұгҖӮ
д»–жү“дәҶдёӘе“Ҳж¬ пјҡвҖңиҖҒзҷҪпјҢдҪ еӣһжқҘе•ҰгҖӮдёҚиҜҙжҳҺеӨ©еҺ»дјҗжңЁеҗ—пјҹеҜ№дәҶпјҢйӮЈз“®йҮҢдёҚжҳҜзҺүзұіз§ҚеӯҗпјҢе’ұеҗғдёҚзқҖзӘқеӨҙдәҶгҖӮе…ҲзқЎеҗ§пјҢжҳҺе„ҝеңЁжғіеҠһжі•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ҝ»дәҶдёӘиә«пјҢе°ұеҗ¬иә«еҗҺдёҖдёӘеҶ°еҮүзҡ„еЈ°йҹідј жқҘпјҡвҖңдҪ жҠҠжҲ‘иҷҸеҲ°жӯӨең°пјҢдҪ еҫ—иҙҹиҙЈжҠҠжҲ‘йҖҒеӣһеҺ»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иҝҷжүҚжҳҺзҷҪпјҢеҺҹжқҘпјҢдёҚжҳҜзҷҪеӯЈд№қпјҢиҖҢжҳҜзҝ еұҸеұұзҡ„йӮЈе§‘еЁҳеҸҲеӣһжқҘдәҶгҖӮ
ж”Ҝж№ғзңјзқӣд№ҹдёҚзқҒпјҡвҖңдҪ дёҚжҳҜжңүдёҖеЎ”еёғеҗ—пјҢеә”иҜҘеӨҹдҪ з§ҹжқЎе°ҸиҲ№дәҶгҖӮеҰӮжһңдёҚеӨҹпјҢдҪ е°ұе…ҲеҪ“е®ҡйҮ‘з”ЁпјҢеҲ°дәҶдҪ 们зҝ еұҸеұұпјҢз»ҷиЎҘйҪҗд№ҹе°ұжҳҜдәҶгҖӮвҖқ
姑еЁҳйҒ“пјҡвҖңеӯӨйӣ¶еІӣзҝ еұҸеұұдё–д»Јдёәд»ҮпјҢжҲ‘иҰҒжҳҜиў«еҲ«дәәеҸ‘зҺ°пјҢеҸӘжңүжӯ»и·ҜдёҖжқЎ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жҢҮдәҶ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еӨҙйЎ¶пјҡвҖңдҪ д№ҹзһ§и§ҒдәҶпјҢжҲ‘иә«ж— еҲҶж–ҮпјҢз©·е…үиӣӢдёҖдёӘпјҢдҪ и®№дёҠжҲ‘д№ҹжІЎз”ЁгҖӮвҖқ
姑еЁҳиө°еҲ°иҚүеёӯеӯҗж—ҒпјҢиёўдәҶиёўж”Ҝж№ғпјҡвҖңдҪ иө·жқҘпјҢеё®жҲ‘жғіжғіеҠһжі•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дёҚиҖҗзғҰзҡ„еқҗиө·иә«пјҡвҖңжҲ‘е°ұзҹҘйҒ“пјҢзӢ—дёҚиғҪе–Ӯеҫ—еӨӘйҘұпјҢдәәдёҚиғҪеҜ№еҘ№еӨӘеҘҪпјҒдҪ жҳҜ蹬鼻еӯҗдёҠи„ёпјҢжҳҜпјҢжҲ‘жңүй”ҷпјҢжҲ‘дёҚиҜҘжҠҠдҪ жүӣеӣһжқҘпјҢеҸҜжҲ‘иғҪжңүд»Җд№ҲеҠһжі•е•ҠпјҹдҪ иө–дёҠжҲ‘д№ҹжІЎз”ЁпјҒвҖқ
иҝҷ姑еЁҳеҖ”ејәең°жҳӮзқҖеӨҙпјҡвҖңжҲ‘жІЎиө–дҪ гҖӮвҖқ
иҜҙе®ҢпјҢ姑еЁҳиө°еҲ°йӮЈжңЁжқҝжЎҢж—ҒеқҗеңЁең°дёҠпјҢй—ӯзӣ®е…»зҘһгҖӮ
ж”Ҝж№ғж°”жҖҘиҙҘеқҸзҡ„жҠ“еј„иҮӘе·ұзҡ„еӨҙеҸ‘пјҢз«ҷиө·иә«иө°еҲ°жңЁжқҝжЎҢеүҚпјҢжҠҠзў—зӯ·ж”¶жӢҫдәҶдёҖдёӢпјҢжҗ¬иө·жңЁжқҝеҲ°дәҶеұӢй—ЁеҸЈпјҢеӣһиҝҮеӨҙжҢҮдәҶжҢҮиҚүеёӯпјҡвҖң姑еҘ¶еҘ¶пјҢжҲ‘жңҚдәҶпјҢжҲ‘й”ҷдәҶпјҒиЎҢдәҶеҗ§пјҹжңүд»Җд№ҲдәӢе„ҝе’ұжҳҺе„ҝж—©дёҠеҶҚиҜҙпјҢдҪ зқЎиҚүеёӯеҗ§пјҢжҲ‘зқЎиҝҷеқ—е„ҝзЎ¬жқҝгҖӮвҖқ
иҜҙзқҖж”Ҝж№ғиәәеңЁжңЁжқҝдёҠпјҢи„ёжңқеӨ–пјҢиғҢжңқйҮҢпјҢзҒҜд№ҹжІЎйЎҫеҫ—дёҠеҺ»еҗ№зҒӯпјҢе°ұй—ӯдёҠдәҶзңјгҖӮ
姑еЁҳд№ҹдёҚе®ўж°”пјҢеқҗеңЁдәҶиҚүеёӯдёҠгҖӮиҚүеёӯе·Із»Ҹиў«ж”Ҝж№ғз»ҷжҚӮжҡ–дәҶпјҢеҘ№д»ҺжҖҖйҮҢжҺҸеҮәзў—еҸЈеӨ§зҡ„дёҖеқ—е„ҝзӮ№еҝғпјҢе°ҸеҸЈеҗғзқҖгҖӮ
дәәзҡ„ж¬ІжңӣжҳҜж— жі•иў«еҪ»еә•еҺӢжҠ‘зҡ„пјҢиў«еҺӢжҠ‘зҡ„ж—¶еҖҷжңҖзҒөж•Ҹзҡ„е°ұжҳҜе—…и§үе’ҢжғіиұЎеҠӣгҖӮдәәеңЁзҰҒж¬І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ејӮжҖ§иә«дёҠдёҖзӮ№зӮ№ж·Ўж·ЎйҰҷж°ҙе‘іпјҢжҲ–иҖ…еҺҹе§Ӣзҡ„жұ—ж°ҙзҡ„е‘ійҒ“пјҢйғҪдјҡи®©дәәжө®жғіиҒ”зҝ©пјҢеҜ№ж–№дёҖдёӘзңјзҘһгҖҒдёҖдёӘжүӢеҠҝгҖҒдёҚз»Ҹж„Ҹзҡ„дёҖдёӘеӯ—иҜҚпјҢйғҪдјҡи®©дҪ иў«turn onпјҒиҝһз»“е©ҡд№ӢеҗҺеӯ©еӯҗзҡ„е№је„ҝеӣӯйҖүе“Ә家йғҪејҖе§ӢиҖғиҷ‘дәҶгҖӮ
иҖҢдёҖдёӘдәәйЈҹж¬ІзҲҶжЈҡ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ж’•ејҖдёҖзүҮзІ—зіҷзҡ„йқўеҢ…пјҢдҪ д№ҹиғҪй—»еҲ°ж·Ўж·Ўзҡ„йәҰйҰҷгҖӮж”Ҝж№ғжң¬жқҘиҝ·иҝ·зіҠзіҠе·Із»ҸзқЎзқҖпјҢеҸҜж·Ўж·Ўзҡ„гҖҒз”ңз”ңзҡ„еҫ—йҰҷж°”еҰӮеҗҢиў«йҳҝжӢүдёҒзҘһзҒҜйҮҢеҶ’еҮәжқҘзҡ„жө“зғҹпјҢжІҒе…Ҙд»–зҡ„йј»еӯ”пјҢж”Ҝж№ғзңјзқӣеҝҪ然被зӮ№дә®дәҶгҖӮ
д»–зҝ»иә«еҶІйҮҢпјҢиҖіжңөйҮҢеҗ¬еҲ°дәҶе’Җеҡјзҡ„еЈ°йҹіпјҢиҝҳжңүе–үе’ҷдёӢе’Ҫзҡ„еЈ°йҹіпјҢж”Ҝж№ғзҰҒдёҚдҪҸдҪҝеҠІи·ҹзқҖе’ҪдәҶеҸЈе”ҫжІ«пјҢж”Ҝж№ғзңҜзјқзқҖзңјпјҢзһ§и§ҒйӮЈдёӘеЁҮе°Ҹзҡ„иә«еҪұжӯЈдёҖеҸЈдёҖеҸЈеҗғзқҖдёҖеқ—иҪҜзі•пјҢ姑еЁҳе…¶е®һд№ҹеҸ‘зҺ°ж”Ҝж№ғйҶ’дәҶпјҢжҺ°дәҶдёҖеқ—е„ҝиҪҜзі•ж”ҫеҲ°дәҶиҮӘе·ұйқўеүҚпјҢж„ҸжҖқеҪ“然жҳҜеҫҲжҳҺжҳҫпјҡж—ўдёҚйӮҖиҜ·пјҢд№ҹдёҚжӢ’з»қгҖӮ
ж”Ҝж№ғзҡ„иҮӘе°ҠжҸҗйҶ’д»–пјҢдёҚиҰҒиө·иә«еҺ»еҗғпјҢеҸҜиӮҡеӯҗеңЁжҠ—и®®пјҢеӨ§и„‘еңЁйҖ еҸҚпјҢд»–еҸҲдҪҝеҠІе’ҪдәҶеҸЈе”ҫжІ«пјҢжүӯиҝҮиә«еҺ»пјҢзқЎдәҶгҖӮ
姑еЁҳзҡ„и„ёдёҠпјҢйңІеҮәдәҶдёҖдёқдёҚжҳ“еҜҹи§үзҡ„笑ж„ҸгҖӮ
зӣёе…іжҺЁиҚҗ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иҮӘж•‘з»„з»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жұӮз”ҹ:жҲ‘иҰҒеҪ“еҘізҡ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јҖеӯҰи§үйҶ’еӨҡйЎ№жҠҖиғҪ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иҝҷдёӘдё§е°ёжңүзӮ№жҖ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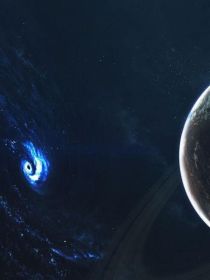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Ҫ’дәҺжҳҹе°ҳ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