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7з« жЁӘз”ҹжһқиҠӮ
жҳҺжңҲеҪ“з©әгҖӮ ж”Ҝж№ғе’Ңзҝ йқ’е°ұеғҸдёҖеҜ№е„ҝйҖғиҜҫзҡ„й«ҳдёӯз”ҹдёҖж ·пјҢеқҗеңЁиҚүдёӣйҮҢпјҢеҗ¬зқҖз§Ӣиҷ«йёЈеҸ«пјҢзңӢзқҖж№–ж°ҙеҘ”жөҒгҖӮ
и®ёд№…пјҢзҝ йқ’жүӯеӨҙзңӢдәҶзңӢж”Ҝж№ғпјҢеҸҲиҪ¬иҝҮеӨҙ继з»ӯзңӢзқҖж№–йқўдёҠжңҲе…үдёӢзҡ„ж¶ҹжјӘгҖӮ
ж”Ҝж№ғж·Ўж·Ўең°иҜҙ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е…¶е®һпјҢжҲ‘зҹҘйҒ“дҪ дёҚеҸ«зҝ йқ’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дёҖж„ЈпјҢжүӢйҮҢжҚ»зқҖиҚүиҢҺй—®пјҡвҖңдҪ жҖҺд№ҲзҹҘйҒ“зҡ„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еҳҝеҳҝдёҖ笑пјҡвҖңдҪ и·ҹжҲ‘иҜҙдҪ зҡ„жқҘеҺҶ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з®ЎйӮЈдёӘиҖҒеӨӘеӨӘеҸ«еӯҷе©Ҷе©ҶпјҢе“Әе„ҝжңүе„ҝеӘіеҰҮз§°е‘је©Ҷе©ҶиҝҳеёҰзқҖ姓ж°Ҹзҡ„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еҫ®еҫ®дёҖ笑пјҡвҖңйӮЈдҪ жҖҺд№ҲдёҚжҲіз©ҝжҲ‘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‘ҮеӨҙпјҡвҖңжІЎеҝ…иҰҒпјҢеҗҚеӯ—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дәәзҡ„д»ЈеҸ·пјҢдёҚз®ЎдҪ еҸ«еј дёүиҝҳжҳҜжқҺеӣӣпјҢдҪ иҝҳжҳҜдҪ пјҢж— жүҖи°“е•Ұ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еҗ¬еҲ°иҝҷеҸҘж— жүҖи°“пјҢеҸҚиҖҢеҝғеӨҙж¶ҢдёҠдёҖз§ҚеӨұиҗҪгҖӮ
ж”Ҝж№ғ继з»ӯ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зңӢеҫ—еҮәжқҘпјҢдҪ иҝҷдёӘдәәе№іж—¶е°ұдёҚзҲұиҜҙиҜқпјҢеҶ·зҫҺдәә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жІЎжҺҘиҝҷдёӘиҜқеӨҙпјҢиҖҢжҳҜй—®йҒ“пјҡвҖңжҲ‘зҺ°еңЁиҝҳжҳҜдёҚжҳҺзҷҪпјҢдҪ еҲ°еә•дёәд»Җд№ҲиҰҒж•‘жҲ‘е‘ў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ӢҚдәҶжӢҚиғёеҸЈпјҡвҖңдёәдәҶеҪ“дёҖдёӘеҘҪдәәе‘җгҖӮиҝҷжңүд»Җд№ҲеҘҮжҖӘзҡ„пјҹвҖқ
вҖңе‘ёпјҒдҪ жүҚдёҚжҳҜеҘҪдәәе‘ўгҖӮвҖқзҝ йқ’иҪ»еЈ°е•җйҒ“гҖӮ
ж”Ҝж№ғд№ҹ笑дәҶпјҡвҖңе“Һе‘ҖпјҢиў«дҪ зңӢз ҙдәҶгҖӮдёҚиҝҮпјҢ既然жҲ‘дёҚжҳҜеҘҪдәәпјҢйӮЈжҲ‘е°ұжҳҜеқҸдәәдәҶпјҹвҖқ
зҝ йқ’еҸҲдёҖж„ЈпјҢеҘ№и„ұеҸЈиҖҢеҮәпјҡвҖңдҪ еҪ“然д№ҹдёҚжҳҜдёӘеқҸдәә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Ҫ иҜҙиҜқжҖ»жҳҜйӮЈд№ҲдёҚзқҖи°ғпјҢжҳҺжҳҺжҳҜеҒҡеҘҪдәӢе„ҝпјҢиҝҳйқһеҫ—жҢ–иӢҰи®ҪеҲәи°ғ笑зҡ„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ңӢеҲ°зҝ йқ’е°ҙе°¬зҡ„ж ·еӯҗпјҢйқһеёёејҖеҝғпјҡвҖңеҜ№е–ҪпјҒеқҸдәәд»ҺжқҘйғҪжҳҜдёҖжң¬жӯЈз»Ҹзҡ„пјҢжҲ‘иҝҷз§ҚпјҢе°ұжҳҜеҲҖеӯҗеҳҙжһңеҶ»еҝғгҖӮвҖқ
вҖңд»Җд№ҲеҸ«жһңеҶ»пјҹвҖқ
вҖңе°ұжҳҜеғҸиұҶи…җдёҖж ·зҡ„пјҢдҪҶжҳҜпјҢжһңеҶ»жҳҜйҖҸжҳҺзҡ„пјҢй—»иө·жқҘжңүдәӣеғҸдҪ з»ҷжҲ‘зҡ„зҷҫиҠұиҶҸгҖӮж°ҙжһңе‘іе„ҝзҡ„гҖӮвҖқ
вҖңдҪ иҝҳжІЎжңүеӣһзӯ”жҲ‘пјҢдҪ еҲ°еә•дёәд»Җд№Ҳж•‘жҲ‘пјҹвҖқзҝ йқ’еҲЁж №е„ҝй—®еә•гҖӮ
ж”Ҝж№ғд»Һи„ҡдёӢжҠ“дәҶдёҖеҸӘиҹӢиҹҖпјҢеӣһзӯ”йҒ“пјҡвҖңдҪ иҝҷд№ҲеҘҪзңӢпјҢиҝҷд№ҲжјӮдә®пјҢжҲ‘иӮҜе®ҡжҳҜеӣҫдҪ зҡ„е®№иІҢе‘—пјҢеҰӮжһңдҪ иҗҪеҲ°дәҶеқҸдәәжүӢйҮҢпјҢйӮЈдёҚе°ұеҸҜжғңдәҶеҳӣгҖӮвҖқ
иҝҷеӣһзӯ”и®©зҝ йқ’е“ӯ笑дёҚеҫ—пјҢж„ҹеҠЁдёҚеҫ—пјҢд№ҹз”ҹж°”дёҚеҫ—гҖӮ
ж”Ҝж№ғжҠҠиҹӢиҹҖж”ҫеҲ°ең°дёҠпјҢиҹӢиҹҖи№Ұи№Ұе“’е“’зҡ„и·іиө°дәҶгҖӮд»–жҗ¬иө·и„ё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жҲ‘жңүдёӘдәӢе„ҝиҰҒдҪ её®жҲ‘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иҪ»еЈ°е“јдәҶдёҖдёӢпјҡвҖңе°ұзҹҘйҒ“дҪ дјҡжңүжүҖеӣҫзҡ„пјҢдҪ иҜҙеҗ§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ж·ұеҗёдёҖеҸЈж°”пјҢж’…иө·еҳҙеҗ№дәҶеҗ№иҮӘе·ұзҡ„еӨҙеҸ‘еёҳе„ҝпјҢ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дҪ еӣһеҲ°зҝ еұҸеұұд»ҘеҗҺпјҢйә»зғҰдҪ её®жҲ‘жү“еҗ¬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д»–еҸ«иҺ«е°ҸеҲҷпјҢеҰӮжһңжүҫеҲ°дәҶпјҢдҪ и®©д»–жқҘиҸҠиҠұеә„жүҫжҲ‘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дҪҺдёӢеӨҙпјҢеЈ°йҹіеҫҲдҪҺеҫҲдҪҺең°еӣһйҒ“пјҡвҖңжҲ‘зӯ”еә”дҪ пјҢдёҖе®ҡеё®дҪ жүҫгҖӮиҝҷдёӘиҺ«е°ҸеҲҷпјҢжҳҜз”·зҡ„еҘізҡ„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ү‘哧дёҖ笑пјҡвҖңд»–еҪ“然жҳҜвҖҰвҖҰвҖқ
ж”Ҝж№ғеҝҪ然жғіеҲ°пјҢиҝҷиҝҳзңҹдёҚеҘҪиҜҙпјҢеӣ дёәзҷҪеӯЈд№қжҳҜзәҜзҲ·д»¬пјҢзәҜзҡ„пјҢеҸҜжқҘеҲ°иҝҷе„ҝжҲҗдәҶеЁҮдҝҸзҡ„е°Ҹе°‘еҰҮдәҶпјҢи°ҒзҹҘйҒ“иҺ«е°ҸеҲҷеҲ°дәҶиҝҷдёӘдё–з•ҢпјҢжҳҜз”·жҳҜеҘіпјҢжҳҜиҖҒжҳҜе°‘е‘ўгҖӮ
ж”Ҝж№ғжҢ дәҶжҢ еӨҙпјҡвҖңеә”иҜҘжҳҜз”·зҡ„пјҢд№ҹеҸҜиғҪжҳҜеҘізҡ„гҖӮжҲ‘иҜҙдёҚеҘҪ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зәій—·ең°й—®пјҡвҖңдҪ дҝ©жІЎи§ҒиҝҮ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ҢҮдәҶ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и„ҡпјҡвҖңжғ…еҗҢжүӢи¶іпјҢиҝҮе‘Ҫзҡ„дәӨжғ…гҖӮвҖқ
вҖңйӮЈдҪ жҖҺд№ҲдёҚзҹҘйҒ“д»–жҳҜз”·жҳҜеҘіе‘ўпјҹвҖқ
вҖңдёүиЁҖдёӨиҜӯжҲ‘з»ҷдҪ и§ЈйҮҠдёҚжё…пјҢдҪ е°ұз•ҷж„ҸдёӢпјҢеё®жҲ‘жүҫжүҫеҗ§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й»ҳй»ҳзӮ№еӨҙпјҢжүӢйҮҢдёҖзӣҙжҚ»зқҖдёҖж №иҚүпјҢж”Ҝж№ғжҢҮдәҶжҢҮпјҡвҖңжҲ‘д»ҘиҚүдёәйўҳпјҢз»ҷдҪ еҒҡйҰ–иҜ—еҗ§гҖӮеҗ¬еҘҪдәҶе•Ҡпјҡз–ҫйЈҺзҹҘеҠІиҚү,дёҖеІҒдёҖжһҜиҚЈпјҢйҮҺзҒ«зғ§дёҚе°ҪпјҢж¶Ұзү©з»Ҷж— еЈ°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йЎәеҳҙиғЎзј–д№ұж”’пјҢзҝ йқ’зҡ„еҝғжҖқжІЎеңЁиҝҷе„ҝпјҢеҘ№й—®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жҲ‘жүҫеҲ°дәҶйӮЈдёӘиҺ«е°ҸеҲҷпјҢжҲ‘е°ұиҜҙиҸҠиҠұеә„зҡ„жЎ‘е…ЁеҶҚжүҫд»–пјҢеҜ№еҗ—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’Үж’ҮеҳҙпјҡвҖңдҪ зңӢдҪ иҝҷдё«еӨҙпјҢжғізҹҘйҒ“жҲ‘зңҹе®һзҡ„еҗҚеӯ—пјҢдҪ е°ұзӣҙиҜҙе‘—пјҢжӢҗејҜжҠ№и§’е№Іеҳӣе‘ҖгҖӮжҲ‘еҸ«ж”Ҝж№ғпјҢдҪ и·ҹд»–иҜҙж”Ҝж№ғеңЁжүҫд»–гҖӮвҖқ
вҖңйӮЈдёәд»Җд№ҲеҲ«дәәз®ЎдҪ еҸ«жЎ‘е…Ёе‘ўпјҹдҪ еҲ°еә•е§“жЎ‘иҝҳжҳҜ姓ж”ҜпјҹвҖқ
вҖңдҪ жҳҜеҚҒдёҮдёӘдёәд»Җд№Ҳе‘ҖпјҹеҲЁж №й—®еә•д№ҹжІЎдҪ иҝҷж ·еҫҖзҘ–еқҹдёҠеҲЁзҡ„е‘ҖпјҒвҖқж”Ҝж№ғд»ҺжҖҖйҮҢжҺҸеҮәдёҖдёӘжІ№зәёеҢ…пјҢвҖңжҲ‘д№ҹжІЎд»Җд№ҲеҸҜйҖҒдҪ зҡ„пјҢиҝҷжҳҜй…ұзүӣиӮүпјҢдҪ еңЁи·ҜдёҠеҗғеҗ§гҖӮвҖқ
жІЎзӯүзҝ йқ’жҺҘпјҢж”Ҝж№ғеҝҪ然дёҖжҢҮпјҡвҖңдҪ зһ§пјҢжңүе°ҸиҲ№жқҘдәҶпјҢиҲ№дёҠзӮ№зқҖзҒҜе‘ў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дёҫзӣ®и§Ӯзһ§пјҢжһң然пјҢдёҖеҸ¶е°ҸиҲҹйЈҳйЈҳиҚЎиҚЎз”ұиҝңеӨ„ж…ўж…ўеңЁйқ иҝ‘пјҢеҘ№жғіз«ҷиө·иә«е–ҠпјҢж”Ҝж№ғжҢүдҪҸеҘ№зҡ„иӮ©иҶҖпјҢеҸҲеҳҳдәҶдёҖеЈ°пјҡвҖңе’ұдҝ©д»ҺзӘқжЈҡйҮҢйҖғеҮәжқҘпјҢжҲ‘жҖ•жңүдәәеӣӣеӨ„жҗңеҜ»пјҢи°Ғ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дҪ 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дҪ е…ҲеқҗеңЁиҝҷе„ҝзӯүзқҖпјҢжҲ‘еҺ»е’Ңиҝҷе°ҸиҲ№жҺҘеӨҙ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д»ҺжҖҖйҮҢж‘ё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жҠҠе°ҸеҲҖпјҢдёҖжүҺжқҘй•ҝпјҢжҹіеҸ¶зҡ„еҪўзҠ¶гҖӮж”Ҝж№ғеҸ№ж°”иҜҙпјҡвҖңиҝҷз ҙзҺ©ж„ҸеҲҮиұҶи…җйғҪдёҚеӨҹдҪҝзҡ„пјҢжҲ‘дёҚз”ЁйҳІиә«гҖӮвҖқ
жІЎжғіеҲ°пјҢзҝ йқ’жҳҜжӢҪдәҶдёҖжқЎжҹіж ‘жһқпјҢжҠҠжҹіжһқз”Ёе°ҸеҲҖеҲҮдәҶдёҖе°ҸжҲӘпјҢжҠҠиҝҷжҲӘжҹіжһқжҸүдәҶеҸҲжҸүпјҢжҚ»дәҶеҸҲжҚ»пјҢжҹіж ‘зҡ®ж•ҙдёӘе°ұдёӢжқҘдәҶгҖӮжҠҠдёҖз«ҜеүІе№іж•ҙпјҢи–„и–„зҡ„еүҠдәҶжҢҮз”ІжңҲзүҷзҷҪйӮЈд№ҲдёҖе°Ҹж®өгҖӮж”ҫеҲ°еҳҙйҮҢпјҢиҪ»иҪ»дёҖеҗ№пјҢиҝҷеңҶзӯ’жҹіж ‘зҡ®еҸ‘еҮәдәҶе“Ёеӯҗзҡ„еЈ°е“ҚгҖӮ
ж”Ҝж№ғзңӢеҫ—зӣҙжӢҚеӨ§и…ҝпјҡвҖңжҲ‘ж“Ұе’§пјҢдёҚеҗҢзҡ„дё–з•ҢпјҢдёҖж ·зҡ„з«Ҙе№ҙе•ҠгҖӮвҖқ
зҝ йқ’жҠҠиҝҷз®Җжҳ“е“ЁеӯҗйҖ’з»ҷж”Ҝж№ғпјҡвҖңдҪ еҲ°еІёиҫ№пјҢеҗ№жҡ—еҸ·пјҢдёүеЈ°й•ҝзҡ„пјҢдёӨеЈ°зҹӯзҡ„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Ө§йӘӮпјҡвҖңи°Ғи®ҫзҪ®зҡ„иҝҷжҡ—еҸ·е•ҠпјҢдёүй•ҝдёӨзҹӯпјҢиҝҷж–№дәәиҙҘ家зҡ„еҖ’йңүеӮ¬зҡ„дёҚеҗүеҲ©зҡ„гҖӮе“ҺеҜ№дәҶпјҢдҪ еҲҡжүҚз”Ёеҳҙеҗ№дәҶиҝҷиҫ№пјҢжҲ‘еҶҚеҗ№еҫ—иҜқ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°ұд»ЈиЎЁе’ұдҝ©дәІеҳҙдәҶпјҹвҖқ
зҝ йқ’дёҫиө·жҹіеҸ¶еҲҖзӣҙеҲәж”Ҝж№ғпјҢж”Ҝж№ғж—©жңүйҳІеӨҮпјҢеҒ·з¬‘зқҖзҢ«зқҖи…°еҘ”еҗ‘дәҶеІёиҫ№гҖӮжҠҠдёҖдёӘзҫһеҫ—ж— ең°иҮӘе®№зҡ„зҝ йқ’з•ҷеҲ°дәҶиҚүдёӣдёӯгҖӮ
ж”Ҝж№ғеҲ°дәҶеІёиҫ№пјҢеҶІзқҖиҝңеӨ„зҡ„е°ҸиҲ№жҢҘжүӢпјҢеҳҙйҮҢдёүй•ҝдёӨзҹӯең°еҗ№зқҖпјҢ еҗ№еҫ—и…®её®еӯҗз”ҹз–јпјҢеӣ дёәзјәж°§пјҢзңјеүҚйғҪеҶ’йҮ‘жҳҹдәҶпјҢз»ҲдәҺжңүеҠЁйқҷдәҶгҖӮ
еҸӘи§Ғж”Ҝж№ғе·ҰеҸідёӨдҫ§зҡ„жө…ж°ҙеӨ„пјҢдёүиүҳеӨ§иҲ№дә®иө·дәҶзҒ«е…үзҒҜе…үпјҢеӨ§иҲ№жү¬еёҶиө·й”ҡпјҢеҶІзқҖе°ҸиҲ№еҢ…жҠ„иҝҮеҺ»пјҢе°ҸиҲ№дёҠзҡ„дәәи§ҒеҠҝдёҚеҰҷпјҢ马дёҠзҶ„зҒӯдәҶзҒҜзҒ«пјҢи°ғиҪ¬иҲ№еӨҙпјҢеҫҖеҢ—驶еҺ»вҖҰвҖҰ
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ж”Ҝж№ғиә«еҗҺпјҢжңүдёҖдјҷдәәзӮ№дәҶзҒ«жҠҠжҠҠж”Ҝж№ғеӣўеӣўеӣҙдҪҸгҖӮ
ж”Ҝж№ғдёҖзһ§пјҢдёәйҰ–зҡ„жӯЈжҳҜжЎғиҠұеә„зҡ„еә„дё»йҷ¶йҡҗпјҢд»–иә«иҫ№зҡ„ж—ўжңүе…іжҠјиҮӘе·ұзҡ„зҳёеӯҗпјҢеҸҲжңүеҲҖз–Өи„ёпјҢиҝҳжңүеҮ дёӘз©ҝз»ёиЈ№зјҺзҡ„пјҢзңӢж ·еӯҗпјҢеә”иҜҘжҳҜеә„йҮҢзҡ„йҷўдё»гҖӮ
еҲҖз–Өи„ёжӢҺзқҖж–§еӯҗиө°иҝҮжқҘпјҡвҖңжЎ‘е…ЁпјҢеӨ§жҷҡдёҠи·‘еҲ°ж№–иҫ№е№ІеҳӣжқҘе•Ұ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иӢҘж— е…¶дәӢең°жҢҮдәҶжҢҮеӨ©дёҠзҡ„жңҲдә®пјҡвҖңй•ҝеӨңжј«жј«пјҢж— еҝғзқЎзң пјҢжҳҺжңҲеҪ“дёӯпјҢд№җеңЁе…¶дёӯпјҢиүҜиҫ°зҫҺжҷҜпјҢжҲ‘е…ҪжҖ§еӨ§еҸ‘пјҢдёҚеҜ№пјҢжҲ‘иҜ—жҖ§еӨ§еҸ‘пјҢжқҘеңЁж№–иҫ№пјҢжғіиҰҒеҗҹиҜ—дёҖйҰ–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жғійғҪжІЎжғіпјҢз«ҹ然жҳҜи„ұеҸЈиҖҢеҮәпјҡвҖңжҜ•з«ҹеҢ—ж№–д№қжңҲдёӯпјҢйЈҺе…үдёҚдёҺеӣӣж—¶еҗҢпјҢдёҖиҪ®жҳҺжңҲжӯЈз©әжӮ¬пјҢиҖҒеӯҗе№Іе•ҘдҪ е°‘з®ЎпјҒжҖҺд№Ҳж ·пјҢиҝҷиҜ—еҒҡзҡ„ж–ҮйҮҮйЈһжү¬еҗ§пјҹжғҠеӨ©ең°жіЈй¬јзҘһдәҶеҗ§пјҹвҖқ
еҲҖз–Өи„ёжҺӮзқҖж–§еӯҗеҶ·еҶ·йҒ“пјҡвҖңжЎ‘е…ЁпјҢиҜҙдҪ жҳҜзҝ еұҸеұұзҡ„еҘёз»Ҷжҡ—жҺўпјҢдҪ зҹўеҸЈеҗҰи®ӨпјҢзҺ°еңЁпјҢдҪ еӨ§еҚҠеӨңзҡ„и·‘еҲ°еІёиҫ№жқҘе’Ңзҝ еұҸеұұзҡ„дәәжҺҘеӨҙиҒ”з»ңпјҢеӨ§е®¶йғҪзңӢеҲ°дәҶпјҢдҪ дёҚжҳҜиҰҒдәәиҜҒеҗ—пјҹзҺ°еңЁжңүдәҶпјҢдҪ иҝҳжңүд»Җд№ҲиҜқиҜҙ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д»°зқҖи„–еӯҗзңӢеӨ©пјҡвҖңжҲ‘жҷҡдёҠеҮәжқҘж•ЈжӯҘиөҸжңҲжҠ“иҹӢиҹҖйҖ®иӣҗиӣҗпјҢи°ҒиҜҙжҲ‘жҳҜжқҘжҺҘеӨҙзҡ„пјҹвҖқ
вҖңеҳҙиҝҳиҝҷд№ҲзЎ¬е•Ҡпјҹд»ҠеӨ©дёӢеҚҲпјҢзҝ еұҸеұұзҡ„жҲҳиҲ№жқҘж”»жү“иҸҠиҠұеә„пјҢе’ҢдҪ зәҰе®ҡдәҶеӨңйҮҢзӣёи§ҒпјҢдҪ д»ҘдёәжҲ‘дёҚзҹҘйҒ“еҗ—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иЈ…дҪңжҒҚ然еӨ§жӮҹпјҡвҖң既然дҪ зҹҘйҒ“пјҢиҜҙжҳҺдҪ е’Ңзҝ еұҸеұұжңүдёҖи…ҝе‘ҖпјҢеҜ№еҗ§пјҹвҖқ
еҲҖз–Өи„ёйқ’зӯӢжҡҙзӘҒпјҡвҖңдҪ ж”ҫеұҒпјҒиЎҖеҸЈе–·дәәпјҒдҪ еҲҡжүҚеҗ№жҹіз¬ӣпјҢдёүй•ҝдёӨзҹӯпјҢд»Җд№Ҳж„ҸжҖқ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еӣһйҒ“пјҡвҖңжІЎж„ҸжҖқе•ҠпјҢж— иҒҠе•ҠпјҢжҲ‘еҳҙе·ҙеҜӮеҜһпјҢеҝғйҮҢеӯӨзӢ¬пјҢи°ҒиҜҙдёҚи®©еҗ№жҹіз¬ӣзҡ„пјҹи°Ғ规е®ҡдәҶеҗ№зҡ„ж—¶еҖҷеҮ й•ҝеҮ зҹӯиҝҳзҠҜжі•зҡ„пјҹвҖқ
еҲҖз–Өи„ёиў«ж”Ҝж№ғз»ҷжҢӨе…‘зҡ„йқўзәўиҖіиөӨгҖӮйҷ¶йҡҗеә„дё»иө°еҲ°иҝ‘еүҚпјҡвҖңжЎ‘е…ЁпјҢжҲ‘еҠқдҪ иҝҳжҳҜжүҝи®ӨдәҶзҡ„еҘҪ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пјҡвҖңдҪ жҙҫжҲ‘еҺ»жҡ—жқҖжң¬ең°зҡ„йғЎдё»пјҢдҪ еҪ“зқҖеӨ§дјҷиҜҙпјҢдҪ жүҝи®Өеҗ—пјҹвҖқ
иҝҷиҜқдёҖиҜҙпјҢйҷ¶йҡҗжӢіеӨҙеҸҜж”Ҙзҙ§дәҶпјҢзңјзҘһдёӯд№ҹеҶ’еҮәдәҶжқҖжңәпјҢеӣ дёәд»–зЎ®е®һжҳҜжңүжӯӨжү“з®—пјҢиҖҢдё”пјҢжӯЈеңЁиҗҪе®һпјҢжІЎжғіеҲ°иў«ж”Ҝж№ғиғЎиҜҙе…«йҒ“з»ҷи’ҷеҮҶдәҶпјҢд»–е’¬зқҖзүҷзӮ№еӨҙпјҡвҖңеҘҪпјҢдҪ иҝҳзңҹжҳҜдјҡеҖ’жү“дёҖиҖҷпјҢйӮЈе°ұжҖӘдёҚеҫ—жҲ‘дәҶпјҢжқҘпјҢжҚҶдәҶ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дёҖж‘ҶжүӢпјҡвҖңдё”ж…ўпјҒжҲ‘й—®дҪ пјҢз»ҷжҲ‘е®ҡзҪӘпјҢи°ҒиҜҙдәҶз®—пјҢи°ҒеҒҡдё»пјҹвҖқ
йҷ¶йҡҗеҳҝеҳҝеҶ·з¬‘пјҡвҖңиҸҠиҠұеә„зҡ„дәӢпјҢй„ҷдәәе°ұиғҪеҒҡдё»пјҒвҖқ
вҖңдёәд»Җд№ҲдҪ еҒҡдё»пјҹвҖқ
вҖңеӣ дёәжҲ‘жҳҜеә„дё»пјҹвҖқ
вҖңеҮӯд»Җд№ҲдҪ еҪ“еә„дё»пјҹвҖқ
йҷ¶йҡҗжҢҮдәҶжҢҮиҮӘе·ұи„‘иўӢдёҠйӮЈеӣӣдҪҚж•°пјҡвҖңе°ұеҮӯиҝҷ5000еӨҡеЎ”еёғгҖӮвҖқ
вҖңиҖҒеӯҗиҰҒжҳҜжҜ”дҪ еЎ”еёғиҝҳеӨҡе‘ўпјҹвҖқ
йҷ¶йҡҗдёҖж„ЈпјҢд»–дёҚзҹҘйҒ“ж”Ҝж№ғиҝҷдёӘиҜқд»Җд№Ҳж„ҸжҖқпјҢд»–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йқўеүҚиҝҷдёӘ桑全究з«ҹз§ҒдёӢйҮҢе’Ңзҝ еұҸеұұзҡ„дәәиҫҫжҲҗдәҶд»Җд№Ҳж ·зҡ„дәӨжҳ“гҖӮйҷ¶йҡҗеӣһиҝҮеӨҙзңӢдәҶзңӢиә«иҫ№дәәпјҢжүӯиҝҮи„ёжқҘдёҖеӯ—дёҖйЎҝең°еӣһзӯ”пјҡвҖңйЈҳйӣ¶еІӣзҡ„规зҹ©пјҢеҸӘиҰҒдҪ и¶…иҝҮжҲ‘зҡ„еЎ”еёғпјҢдҪ е°ұжҳҜеә„дё»пјҢдҪ иҜҙдәҶз®—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Ӯ№зӮ№еӨҙпјҡвҖңеҷўпјҢжҳҜиҝҷд№ҲеӣһдәӢе„ҝе•ҠпјҢжҲ‘е°ұйҡҸдҫҝй—®й—®гҖӮвҖқ
дёҖеҸҘиҜқжҠҠйҷ¶йҡҗз»ҷж°”зҡ„иҰҒеҸ‘з–ҜгҖӮ
ж”Ҝж№ғжҺҗзқҖи…°пјҡвҖңдҪ з»ҷжҲ‘е®ҡдәҶзҪӘпјҢиҖҒеӯҗиҰҒжҳҜдёҚжңҚе‘ўпјҹвҖқ
вҖңйӮЈе°ұиҰҒдј—е®ЎдәҶпјҒиҜ·еҮәеӣӣеҚҒдҪҚеҫ·й«ҳжңӣйҮҚзҡ„йҷўдё»е’Ңеә„дё»пјҢеӨ§е®¶дёҖиө·иЈҒе®ҡгҖӮвҖқ
вҖңеҘҪпјҢжҲ‘еҶіе®ҡдәҶпјҢиҜ·д»–们жқҘеҗ§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Ө§иЁҖдёҚжғӯзҡ„иҜқпјҢжҠҠеңЁеңәжүҖжңүдәәйғҪз»ҷж°”д№җдәҶгҖӮеҲҖз–Өи„ёз”Ёж–§еӯҗе°–жҢҮдәҶжҢҮж”Ҝж№ғпјҡвҖңдҪ д№ҹй…ҚпјҒдҪ е…ҲжӢҝеҮәжқҘ40еЎ”еёғ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笑дәҶпјҡвҖңжҲ‘жҠҠиҮӘе·ұеҚ–дәҶпјҢеҚ–з»ҷз…ӨзӘ‘пјҢжҲ‘дёӢеҚҠиҫҲеӯҗе°ұеҺ»жҢ–з…ӨпјҢжҖ»иғҪжҢЈеҫ—дәҶеӣӣеҚҒеЎ”еёғпјҢиҖҒеӯҗдёҚи’ёйҰ’еӨҙдәүеҸЈж°”пјҒвҖқ
йҷ¶йҡҗдёҖи§ҒпјҢиҝҷж”Ҝж№ғйҷӨдәҶеҳҙзЎ¬пјҢжІЎд»Җд№Ҳзңҹжң¬йўҶпјҢд№ҹжІЎд»Җд№ҲеҗҺеҸ°пјҢеҝғе°ұж”ҫдёӢдәҶпјҡвҖңжЎ‘е…Ёе•ҠпјҢе°ұеҮӯзқҖдҪ иҝҷеҮ еӨ©зҡ„жүҖдҪңжүҖдёәпјҢдј—е®Ў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иӮҜе®ҡиҝҳжҳҜжҠҠдҪ еҲӨдёәеҘёз»Ҷзҡ„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еҗҗдәҶеҸЈе”ҫжІ«пјҡвҖңиЎҢе•ҠпјҢйӮЈиҖҒеӯҗе°ұе’ҢдҪ дёҖиө·еӨ©иҜҖпјҒвҖқ
иҝҷиҜқеҸҜжҠҠйҷ¶йҡҗеҗ“еқҸдәҶпјҢд»ҺжқҘе°ұжІЎжңүдәәиҝҷд№Ҳе№ІиҝҮпјҢиҜ·еӨ©иҜҖзҡ„иҜқпјҢж— и®әи°ҒеҜ№и°Ғй”ҷпјҢеӯ°жҳҜеӯ°йқһпјҢйӮЈеҺҹе‘Ҡиў«е‘ҠйғҪеҫ—жӯ»пјҢжӯ»зҡ„жһҒе…¶зј“ж…ўпјҢжһҒе…¶з—ӣиӢҰгҖӮ
йҷ¶йҡҗеңЁз§ӢйЈҺдёӯз«ҹ然еҮәдәҶдёҖиә«еҶ·жұ—пјҢд»–дёҮжІЎжғіеҲ°йқўеүҚиҝҷдёӘжЎ‘е…Ёз«ҹ然жҜ”зӢ—жҖҘи·іеўҷиҝҳжҳҜиҝҮеҲҶгҖӮ
йҷ¶йҡҗжҡ—жғіпјҡвҖңйҡҫйҒ“зңҹзҡ„еҶӨжһүдәҶд»–дәҶпјҹвҖқ
еҲҖз–Өи„ёеҲ°дәҶйҷ¶йҡҗиә«иҫ№иҖіиҜӯдәҶеҮ еҸҘпјҢйҷ¶йҡҗе’¬зқҖзүҷзӮ№дәҶзӮ№еӨҙгҖӮ
еҲҖз–Өи„ёжҠҠж–§еӯҗжһ¶еҲ°ж”Ҝж№ғзҡ„и„–еӯҗдёҠпјҡвҖңжЎ‘е…ЁпјҢдҪ еҫ—дәҶеӨұеҝғз–ҜдәҶпјҢеҚұе®ізӣёйӮ»пјҢзҪӘдёҚе®№иөҰпјҢжқҘпјҢе…ҲжҠҠд»–жү“жҷ•пјҢиЈ…еҲ°иўӢеӯҗйҮҢпјҢжү”еҲ°ж№–йҮҢж·№жӯ»еҫ—дәҶгҖӮвҖқ
е·ҰеҸіеҫҖдёҠеҶІпјҢж”Ҝж№ғдёҮжІЎжғіеҲ°дјҡжңүиҝҷд№ҲдёҖеҮәпјҡвҖңжҸЎиҚүпјҒдҪ 们дёҚжҢүеҘ—и·ҜеҮәзүҢе‘ҖпјҢиҖҚиө–жІЎиҝҷд№ҲиҖҚзҡ„еҗ§пјҹеӨӘй»‘дәҶеҗ§пјҹеӨӘйҳҙжҚҹдәҶеҗ§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ҢЈжүҺ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ҚүдёӣдёӯжңүдәәеҺүеЈ°еӨ§е–Ҡ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дҪҸжүӢпјҒвҖқ
зӣёе…іжҺЁиҚҗ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иҮӘж•‘з»„з»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жұӮз”ҹ:жҲ‘иҰҒеҪ“еҘізҡ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јҖеӯҰи§үйҶ’еӨҡйЎ№жҠҖиғҪ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иҝҷдёӘдё§е°ёжңүзӮ№жҖ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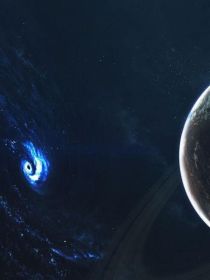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Ҫ’дәҺжҳҹе°ҳ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