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8з« иҜқдёҚжҠ•жңә
еҗ¬иҜҙж”Ҝж№ғиҰҒдёҠдёүжҘјеҺ»иҖҚпјҢе°Ҹд»ҷиҙқе’Ңе®Ӣз§ғеӯҗеҮәеҘҮзҡ„дёҖиҮҙпјҡвҖңдёҚиЎҢпјҒвҖқе®Ӣз§ғеӯҗд»ҺеҸЈиўӢйҮҢжҺҸеҮәдёҖж №й»‘иүІд№ҢжңЁзҡ„зӯ№з ҒпјҡвҖңиҝҷжҳҜ100еЎ”пјҢдҪ дёҠжҘјжөӘеҺ»еҗ§пјҒвҖқ
е®Ӣз§ғеӯҗиғҢдёҠеҸЈиўӢпјҢжӢүиө·д»ҷиҙқдёӢжҘје…‘жҚўзӯ№з ҒеҺ»дәҶгҖӮ
ж”Ҝж№ғжүӢйҮҢжҚҸзқҖзӯ№з ҒпјҢй«ҳй«ҳе…ҙе…ҙең°дёҠжҘјгҖӮиҝҳжІЎеҲ°дёүжҘјпјҢе°ұеҗ¬жҘјдёҠйҡҗйҡҗжңүеҸӨзҗҙд№ӢеЈ°пјҢдёҖдёӘжӣјеҰҷзҡ„еҘіеЈ°йЎәзқҖжҘјжўҜйЈҳйЈҳжёәжёәиҖҢжқҘпјҡ
е°ҳдё–д№Ӣй—ҙдёҮзү©з”ҹпјҢ
йЈһзҰҪиө°е…Ҫеҗ„дёҚеҗҢгҖӮ
е”Ҝжңүдәәз”ҹжңҖеҸҜиҙөпјҢ
еҸҜжҖңдәәз”ҹзҡҶиӢҰжғ…вҖҰвҖҰ
еЈ°йҹіеҝҪеӨ§еҝҪе°ҸпјҢеңЁдёқз«№еЈ°дёӯйЈҳйЈҳж‘Үж‘ҮпјҢж”Ҝж№ғиҫ№еҗ¬иҫ№иҝҲжӯҘдёҠжҘјгҖӮ
иө°дёҠеҺ»иҝҷжүҚеҸ‘зҺ°пјҢиҜҙжҳҜдёүеұӮпјҢе…¶е®һпјҢдёүжҘјиҝҷе„ҝ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°ҸйҳҒжҘјпјҢйқўз§ҜдёҚеӨ§пјҢдёҖжқЎиө°е»ҠзӣҙйҖҡдёҖдёӘеҘ—й—ҙпјҢиө°е»ҠйҮҢиҠұиҚүйҒҚеёғпјҢеӣӣж—¶дёҚи°ўд№ӢиҠұпјҢе…«иҠӮдёҚиҙҘд№ӢиҚүпјҢзҗізҗ…ж»Ўзӣ®пјҢиҷҪ然жҳҜз§ӢеӨ©ж—¶иҠӮпјҢдҪҶиҝҷдәӣиҠұиҚүйғҒйғҒи‘ұи‘ұпјҢж¬Јж¬Јеҗ‘иҚЈгҖӮиҚүжңЁи‘іи•ӨпјҢиҠұйҰҷж»ЎжҘјпјҢеҘ—жҲҝзҡ„жҲҝй—ЁејҖзқҖпјҢж”Ҝж№ғд»ҺеӨ–иҫ№еҫҖйҮҢдёҖзһ§пјҢдҪҶи§ҒдёҖеҗҚиә«жқҗеҫ®иғ–зҡ„дәҢе…«дҪідәәжӯЈжҠҡзҗҙеҗҹе”ұпјҢж—Ғиҫ№дҝ©дё«й¬ҹиҜҙжҳҜдјәеҖҷзқҖпјҢе…¶е®һйғҪдҪҺзқҖеӨҙеҝ«зқЎзқҖдәҶгҖӮ
еј№зҗҙзҡ„姑еЁҳжүӢйҮҢдёҠжҢ‘дёӢжҚ»пјҢеҸЈдёӯиҜҙ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жҳҘжЎғз§ӢзҰҫпјҢеҲ«зқЎдәҶпјҢжңүиҙөе®ўзҷ»й—ЁпјҢеҝ«еҺ»жІҸиҢ¶гҖӮвҖқ
дёӨдёӘе°Ҹдё«й¬ҹд»ҺзһҢзқЎдёӯжғҠйҶ’пјҢжҠ¬еӨҙдёҖзһ§пјҢй—ЁеӨ–з«ҷдәҶдёҖдҪҚе…¬еӯҗе“ҘпјҢзңӢз©ҝзқҖжү“жү®жҳҜеҲҶеӨ–з©·й…ёпјҢеҸҜдҪҶеҮЎиғҪзҷ»дёҠдёүжҘјзҡ„пјҢе°ұиҜҙжҳҺжңүиҝҷдёӘиә«д»·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еұӢйҮҢдәәд№ҹдёҚжҖ ж…ўгҖӮжҳҘжЎғиө°еҮәй—Ёе„ҝжқҘж–ҪзӨјиҝҺжҺҘпјҢеҸҰеӨ–дёҖдёӘз§ӢзҰҫз»ҷжІҸж°ҙжіЎиҢ¶гҖӮ
еҫ®иғ–зҡ„姑еЁҳеқҗеңЁеҸӨзҗҙеҗҺиҫ№пјҢ笑зӣҲзӣҲең°жү“жӢӣе‘јпјҡвҖңиҝҷдҪҚе…¬еӯҗпјҢзңӢжқҘд»ҠеӨ©жүӢж°”дёҚй”ҷе‘Җ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д№ҹдёҚе®ўж°”пјҢеқҗеңЁж—Ғиҫ№жӨ…еӯҗдёҠпјҢе–қдәҶеҸЈиҢ¶пјҡвҖң姑еЁҳиҝҷиҜқиҜҙзҡ„пјҢеҸҜжҳҜжңүдәӣдёҚеҺҡйҒ“гҖӮвҖқ
вҖңеҷўпјҢжӯӨиҜқжҖҺж ·пјҢжҲ‘е“ӘйҮҢжҖ ж…ўеҫ—зҪӘе…¬еӯҗдәҶпјҹвҖқиҝҷеҫ®иғ–зҡ„姑еЁҳиҫ№иҜҙиҫ№з«ҷиө·иә«пјҢиө°еҲ°ж”Ҝж№ғж—Ғиҫ№еқҗдёӢгҖӮ
ж”Ҝж№ғеӣһзӯ”йҒ“пјҡвҖңдҪ иҜҙжҲ‘жүӢж°”еҘҪпјҢиЁҖеӨ–д№Ӣж„ҸдёҚ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жҲ‘иҝҷз©·й…ёжЁЎж ·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еӣ дёәеңЁдёӢиҫ№жүӢж°”еҘҪпјҢиөўдәҶдәӣзӯ№з ҒпјҢиҝҷиҫҲеӯҗйғҪжІЎжңәдјҡеҲ°иҝҷе„ҝдёҖзқ№иҠіе®№еҗ—пјҹвҖқ
иғ–姑еЁҳд№ҹдёҚеҗҰи®ӨпјҢжҠҝеҳҙдёҖ笑пјҢд№ҹз«Ҝиө·иҢ¶жқҜжҠҝдәҶдёҖеҸЈгҖӮ
ж”Ҝж№ғй—®пјҡвҖңж•ўй—®е°Ҹе§җиҠіеҗҚе•ҠпјҹвҖқ
ж—Ғиҫ№жҳҘжЎғжҠўзқҖ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жҲ‘家姑еЁҳеҸ«жқҸеӯҗ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ҒҮиЈ…з–‘жғ‘пјҡвҖңжқҸеӯҗпјҹжҖҘжҖ§еӯҗиҝҳжҳҜж…ўжҖ§еӯҗпјҹвҖқ
жҳҘжЎғжҖҘдәҶпјҡвҖңе“Һе‘ҖпјҢдёҖзңӢдҪ е°ұжҳҜдёҚеӯҰж— жңҜд№ӢдәәгҖӮвҖқ
既然被жүЈдәҶеёҪеӯҗдәҶпјҢж”Ҝж№ғе№Іи„Ҷе°ұиЈ…еӮ»е……жҘһпјҡвҖңеҷўпјҹдёҚеӯҰжӯҰжңҜе•ҠиҝҳжҳҜдёҚеӯҰе·«жңҜе•ҠпјҹжҲ‘жҳҜеҫ—жү“и¶ҹжӢіе‘җиҝҳжҳҜи·іеӨ§зҘһе•ҠпјҹвҖқ
жҳҘжЎғзҝ»дәҶдёӘзҷҪзңје„ҝпјҢжІЎзҗҶж”Ҝж№ғгҖӮ
ж”Ҝж№ғз«Ҝиө·иҢ¶жқҜпјҢдҪҝеҠІж»Ӣе„ҝе–Ҫж»Ӣе„ҝе–Ҫе–қж°ҙпјҢе–қе®ҢдәҶпјҢеҸҲз”Ёиў–еӯҗжҠ№дәҶжҠ№еҳҙпјҢй—®пјҡвҖңе…үжңүе–қзҡ„жІЎеҗғе“’пјҹвҖқ
иҜқиҜҙпјҢиҝҷдёӘдё–з•ҢдёҠпјҢдёҚж•ўиҜҙзҷҫеҲҶд№ӢзҷҫпјҢдҪҶзҷҫеҲҶд№Ӣд№қеҚҒд»ҘдёҠзҡ„дәәпјҢйӮЈйғҪжҳҜд»ҘиІҢеҸ–дәәзҡ„пјҢж— и®әеҸӨд»ҠпјҢж— и®әдёӯеӨ–гҖӮ
仨姑еЁҳдёҖзһ§ж”Ҝж№ғиҝҷеүҜз©·й…ёеҫ·иЎҢе’ҢжІЎи§ҒиҝҮдё–йқўзҡ„ж ·еӯҗпјҢжү“еҝғеә•иҶҲеә”и…»жӯӘгҖӮд№ҹжІЎдәәзҗҶд»–пјҢж”Ҝж№ғиҮӘиЁҖиҮӘиҜӯйҒ“пјҡвҖңдәҢжҘјиҝҳйҡҸдҫҝеҗғз®ЎйҘұе‘ўпјҢжҖҺд№ҲеҲ°дәҶдёүжҘјиҝҳдёҚеҰӮжҘјдёӢе‘ўпјҹеҜ№дәҶпјҢжқҸеӯҗ姑еЁҳпјҢдҪ иҝҷеҗҚеӯ—жҲ‘и§үеҫ—еҸҜд»Ҙж”№дёҖдёӢгҖӮвҖқ
жқҸеӯҗи„ёдёҠе Ҷз ҢзқҖиҒҢдёҡжҖ§еҫ®з¬‘пјҡвҖңж„ҝеҗ¬е®ўе®ҳй«ҳи®ә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дёҖеҗ¬пјҢеҡҜпјҢйғҪдёҚз®ЎжҲ‘еҸ«е…¬еӯҗдәҶпјҢж”№еҸ«е®ўе®ҳдәҶпјҢзңӢжқҘиҮӘе·ұиҝҷдёӘеҪўиұЎжҳҜдёҖеӨ©дёҚеҰӮдёҖеӨ©дәҶгҖӮд»–е№Іи„Ҷзҝҳиө·дәҢйғҺи…ҝпјҡвҖңжқҸеӯҗиҝҷеҗҚеӯ—дёҖеҗ¬е°ұеӨӘй…ёдәҶпјҢдҪ зңӢдҪ иҝҷиә«еҪўпјҢиғ–д№Һд№ҺеңҶеў©еў©зҡ„пјҢе°Ҹзҹ®дёӘе„ҝпјҢдҪ еә”иҜҘеҸ«еҢ…еӯҗгҖӮж—Ғиҫ№зҡ„иҝҷдҝ©е‘ўпјҢд№ҹеҲ«еҸ«д»Җд№ҲжҳҘжЎғз§ӢзҰҫзҡ„пјҢж”№еҸ«йҰ’еӨҙгҖҒиҠұеҚ·пјҢиҝҷеӨҡз“·е®һе•Ҡ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иҝҷеј еҳҙпјҢи®ЁеҘҪ姑еЁҳзҡ„ж—¶еҖҷиғҪжҠҠеҜ№ж–№иҜҙзҡ„еҝғиҠұжҖ’ж”ҫгҖҒд№җдёҚеҸҜж”ҜпјҢдёҖж—Ұи®ҪеҲәжҢ–иӢҰиө·жқҘпјҢйӮЈд№ҹжҳҜзңҹдёҚйҘ¶дәәгҖӮ
жқҸеӯҗ收иө·дәҶиҒҢдёҡжҖ§еҒҮ笑пјҢеһӮжүӢз«ҷеңЁж—Ғиҫ№зҡ„жҳҘжЎғдёҖжӢҚжЎҢеӯҗпјҡвҖңе®ўе®ҳиҜ·иҮӘйҮҚпјҒиҝҷйҮҢдёҚжҳҜз§ҰжҘјжҘҡйҰҶеҚ–笑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жҲ‘зӯүиҷҪиҙ«йқһиҙұ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д№ҹжҠҠи„ёдёҠ笑容收иө·пјҡвҖң既然дёҚжҳҜз§ҰжҘјжҘҡйҰҶпјҢйӮЈдҪ еҖ’жҳҜж‘ҶдёҠиүІеӯҗгҖҒзүҢд№қе•ҠпјҢ既然дёҚж‘ҶпјҢиҰҒд№ҲдҪ е°ұеҺ»з«Ҝеҗғзҡ„пјҢиҰҒд№ҲпјҢдҪ е°ұеҗ¬зҲ·йҖ—й—·еӯҗпјҒвҖқ
ж—Ғиҫ№зҡ„з§ӢзҰҫжҳҜдёӘж…ўжҖ§еӯҗиҖҒе®һ姑еЁҳпјҢеҘ№з»ҷз»ӯдёҠиҢ¶ж°ҙпјҡвҖңе…¬еӯҗжҒҜжҖ’пјҢдёҖиҲ¬жқҘзҰҸиҝһеқҠдёүжҘјзҡ„е®ўзҲ·пјҢйғҪе…ҲжҳҜиҒҠиҒҠеӨ©гҖҒеҸҷеҸҷж—§пјҢеҗ¬жҲ‘家姑еЁҳеј№зҗҙе”ұжӣІпјҢд№ӢеҗҺе‘ўпјҢжүӢи°ҲдёӢжЈӢпјҢжҲ–иҖ…е–қй…’иЎҢд»ӨпјҢе–қзҡ„жҳҜжў…еӯҗй…’пјҢиЎҢзҡ„жҳҜйЈһиҠұд»ӨпјҢж„ҝж„ҸзҺ©зүҢжҺ·йӘ°shaiеӯҗпјҢжҲ‘家姑еЁҳиҮӘ然д№ҹжҳҜеҘүйҷӘзҡ„гҖӮвҖқ
иҝҷ姑еЁҳиҜҙзҡ„иҜқиҷҪ然еҫҲжҹ”иҪҜпјҢдҪҶиҜқйҮҢиҜқеӨ–зҡ„ж„ҸжҖқеҫҲжҳҺжҳҫпјҡдҪ е°ұжҳҜдёҖдёӘеңҹеҢ…еӯҗпјҢиҝҷз§Қйӣ…иҮҙзҡ„жғ…и°ғдҪ жҮӮеҳӣпјҹ
ж”Ҝж№ғжӯӘзқҖи„‘иўӢй—®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е‘Ҷзҡ„еӨӘжҷҡдәҶпјҢиҝҮдәҶеӯҗж—¶дәҶпјҢдҪ иҜҙзҡ„йӮЈдәӣе®ўзҲ·пјҢдјҡдёҚдјҡз•ҷе®ҝе‘ў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иҝҷеҸҘиҜқеҸҜжҳҜжҚ…дәҶжқҸеӯҗзҡ„иӮәз®ЎеӯҗпјҢд»–иЁҖеӨ–д№Ӣж„Ҹе°ұжҳҜпјҢдҪ 们иҜҙиҝҷе„ҝдёҚжҳҜз§ҰжҘјжҘҡйҰҶпјҢйӮЈеҰӮжһңдҪ еҚ–笑еҚ–иә«зҡ„иҜқпјҢжңүд»Җд№ҲеҢәеҲ«е‘ўпјҹдёҚе°ұжҳҜеӨҡдәҶдёҖйЎ№иөҢй’ұеҗ—пјҹ
жқҸеӯҗдёҖз”©иў–еӯҗпјҢе–Ҡ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жҳҘжЎғпјҢйҖҒе®ўпјҒвҖқ
иҝҳжІЎзӯүж”Ҝж№ғиҜҙиҜқпјҢжҘјжўҜеҸЈеҷ”зҡ„еҷ”еҷ”пјҢжңүдәәдёҠдәҶдёүжҘјдәҶпјҢж”Ҝж№ғжҡ—жғіпјҡвҖңйҡҫдёҚжҲҗжҳҜд»ҷиҙқе’Ңе®Ӣз§ғеӯҗжқҘдәҶпјҹвҖқ
жүӯеӨҙдёҖзһ§пјҢеҸӘи§ҒдёӨдёүеҗҚдјҷи®ЎжӢҘзқҖдёҖдҪҚдёӯе№ҙз”·еӯҗиҝӣдәҶй—ЁдәҶпјҢжқҸеӯҗе’Ңдҝ©дё«й¬ҹиө·иә«пјҢиө°иҝҮеҺ»иҝҺжҺҘпјҡвҖңй»„йҰҶдё»пјҢжӮЁжҖҺд№ҲжқҘе•ҰпјҹпјҒвҖқ
иў«з§°дҪңйҰҶдё»зҡ„з”·еӯҗзӮ№зӮ№еӨҙпјҢиө°еҲ°ж”Ҝж№ғиҝ‘еүҚпјҢж·ұж–ҪдёҖзӨјпјҡвҖңй„ҷдәәд№ғжҳҜиҝҷеә§зҰҸиҝһеқҠзҡ„дёң家пјҢжҲ‘еҸ«й»„зҰҸиҝһпјҢдёҚзҹҘжңүиҙөе®ўжқҘеҲ°пјҢеӨұзӨјеӨұзӨј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иә«еӯҗйғҪжІЎж¬ пјҢз«Ҝиө·иҢ¶жқҜе–қдәҶдёҖеҸЈпјҢж•…ж„Ҹз”Ёиў–еӯҗеҸҲж“Ұж“ҰеҳҙпјҢз«ҷиө·иә«пјҡвҖңй»„йҰҶдё»зӨјж•°еҫҲе‘Ёе…Ё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пјҢжҲ‘еңЁиҝҷе„ҝдёҚеҸ—ж¬ўиҝҺпјҢеӣһи§Ғеӣһи§ҒпјҒвҖқ
й»„йҰҶдё»е·®зӮ№з–ҜдәҶпјҢд»–зҡ„иҝҷзҰҸиҝһеқҠдёҖеӨңд№Ӣй—ҙжҚҹеӨұдәҶдёӨеҚғеӨҡеЎ”еёғпјҢж №жң¬е°ұжІЎжі•еҗ‘иөөеӨҸйғЎдё»дәӨд»ЈпјҢжҺҘеҲ°дјҷи®Ўзҡ„йҖҡзҹҘпјҢд»–жҳҜжҖҘеҢҶеҢҶиө¶еҲ°иҝҷйҮҢпјҢдёҖи·ҜдёҠд»–д№ҹеңЁдёҚеҒңең°жғіеҠһжі•пјҢйҖҡиҝҮдјҷи®Ўд»–еҫ—зҹҘпјҢиөўиө°е·Ёж¬ҫзҡ„дёҚжҳҜзҶҹе®ўпјҢиҖҢжҳҜйҷҢз”ҹжқҘе®ўпјҢеҰӮжһңпјҢиҝҷд»ЁдәәжүӯеӨҙе°ұиө°дәҶпјҢйӮЈеҸҜиҰҒдәҶдәІе‘ҪдәҶпјҢжүҖд»ҘжӢјжӯ»жӢјжҙ»д№ҹеҫ—жҠҠ他们з•ҷдҪҸпјҢжҠҠдёўдәҶзҡ„иӮҘиӮүеҶҚжҺҸеӣһжқҘпјҢдёҖеҗ¬ж”Ҝж№ғиҝҷиҜқпјҢй»„йҰҶдё»иө¶зҙ§жӢҪдҪҸж”Ҝж№ғзҡ„иў–еӯҗпјҡвҖңе…¬еӯҗз•ҷжӯҘпјҢдёҚзҹҘжӮЁдҪ•еҮәжӯӨиЁҖе•Ҡ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дёҚиҖҗзғҰең°еҸҲеқҗеӣһжӨ…еӯҗпјҢдёҖжҢҮжқҸеӯҗпјҡвҖңиҝҷдёӘеҢ…еӯҗ姑еЁҳиҜҙдәҶпјҢйҖҒе®ўпјҢи®©жҲ‘ж»ҡиӣӢпјҢйҡҫйҒ“иҝҷдёҚжҳҜдёҚж¬ўиҝҺжҲ‘еҗ—пјҹвҖқ
й»„йҰҶдё»жүӯеӨҙзһ§дәҶжқҸеӯҗдёҖзңјпјҢжқҸеӯҗдҪҺзқҖеӨҙдёҚж•ўиЁҖиҜӯпјҢд№ҹдёҚж•ўи§ЈйҮҠгҖӮ
й»„йҰҶдё»ж»Ўи„ёйҷӘ笑пјҡвҖңиҝҷе…¶дёӯпјҢдёҖе®ҡжңүд»Җд№ҲиҜҜдјҡпјҢжӮЁд»ҠеӨ©жүӢж°”иӣ®еҘҪпјҢдёҖжҠҠиөўдёӢдёӨеҚғеЎ”еёғпјҢиҝҷд»ЁиҜҘжӯ»зҡ„еҘҙжүҚжҖҺд№ҲзқҖд№ҹжғіжІҫжІҫжӮЁзҡ„е–ңж°”е„ҝе•ҠпјҒвҖқ
еҝғзӣҙеҸЈеҝ«ең°жҳҘжЎғвҖңе—·вҖқдәҶдёҖеЈ°пјҡвҖңе•ҠпјҹдёӨеҚғпјҹеЎ”еёғпјҹвҖқ
ж”Ҝж№ғжј«дёҚз»Ҹеҝғең°й—®пјҡвҖңеҲҡжүҚиҝҷдҪҚиҠұеҚ·е§‘еЁҳиҜҙд»Җд№Ҳеј№зҗҙдёӢжЈӢпјҢжҲ‘дёҚдјҡпјҢжҲ‘д№ҹеҗ¬дёҚжҮӮпјҢеҸҲиҜҙд»Җд№ҲйЈһиҠұд»ӨпјҢд»Җд№ҲеҸ«йЈһиҠұд»ӨпјҹвҖқ
з§ӢзҰҫиө¶зҙ§и§ЈйҮҠпјҡвҖңе°ұжҳҜе–қй…’иЎҢд»Өж—¶еҖҷзҡ„дёҖдёӘж–Үеӯ—жёёжҲҸпјҢиЎҢйЈһиҠұд»Өзҡ„ж—¶еҖҷеҸҜд»ҘйҖүз”ЁиҜ—иҜҚдёӯзҡ„еҸҘеӯҗпјҢеёҰиҠұе°ұиЎҢ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иӢҘжңүжүҖжҖқпјҢй—®пјҡвҖңеёҰиҠұе°ұиЎҢпјҢйә»иҠұзҲҶзұіиҠұд»Җд№Ҳзҡ„иЎҢеҗ—пјҹвҖқ
з§ӢзҰҫдёҚж•ўеҗұеЈ°пјҢзһ§дәҶзһ§й»„йҰҶдё»пјҢй»„йҰҶдё»йҷӘзқҖ笑пјҡвҖңжӮЁиҜҙиЎҢе°ұиЎҢ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еҫҲж„ҹе…ҙи¶Јзҡ„ж ·еӯҗпјҡвҖңеҘҪпјҢиҝҷдёӘеҘҪпјҢе’ұ们зҺ©зҺ©иҝҷдёӘпјҒвҖқ
жқҸеӯҗеҪ“зқҖдёң家дёҚж•ўйҖ ж¬ЎпјҢејәеҺӢжҖ’зҒ«йҷӘзқҖ笑пјҢ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йӮЈиҙұеҰҫжҲ‘е…ҲжқҘпјҢвҖңжҳҘеҹҺж— еӨ„дёҚйЈһиҠұ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ҳҙйҮҢеҳҖеҳҖе’•е’•пјҡвҖңе•ҶеҘідёҚзҹҘдәЎеӣҪжҒЁпјҢе‘ғпјҢйҡ”жұҹзҠ№е”ұеҗҺеәӯиҠұпјҒвҖқ
ж”Ҝж№ғиғҪеҗҹиҜ—пјҢе·Із»ҸеҮәд№ҺдәҶжүҖжңүдәәзҡ„ж„Ҹж–ҷпјҢиҖҢдё”пјҢиҝҷеҸҘиҜ—иҝҳжҡ—еҗ«зқҖиҙ¬жҚҹжқҸеӯҗзҡ„ж„ҸжҖқпјҢжқҸеӯҗд№ҹдёҚж•ўеҸ‘дҪңпјҢе°ҸеЈ°жҺҘзқҖиЎҢд»ӨпјҡвҖңзү§з«ҘйҒҘжҢҮжқҸиҠұжқ‘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жғід№ҹдёҚжғіпјҡвҖңйңңеҸ¶зәўдәҺдәҢжңҲиҠұ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’ҢжқҸеӯҗдҪ дёҖеҸҘжҲ‘дёҖеҸҘпјҢжңүжқҘжңүеҫҖпјҢи¶ҠеҫҖеҗҺпјҢжқҸеӯҗи¶ҠеҝғжғҠпјҢжІЎжғіеҲ°жҳҜиҮӘе·ұе°Ҹзһ§дәҶзңјеүҚиҝҷдёӘиҗҪйӯ„зҡ„еңҹеҢ…еӯҗгҖӮ
и¶іжңүдёҖеҲ»й’ҹзҡ„еҠҹеӨ«пјҢж”Ҝж№ғеҜ№йҒ“пјҡвҖңзЁ»иҠұйҰҷйҮҢиҜҙдё°е№ҙгҖӮвҖқ
жқҸеӯҗ笑йҒ“пјҡвҖңе…¬еӯҗпјҢиҮӘе·ұйҡҸеҸЈзј–зҡ„иҜ—еҸҘжҳҜдёҚиғҪз®—зҡ„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җ¬дәҶиҝҷиҜқпјҢд»–еҝҪ然жҳҺзҷҪдәҶпјҢеҚ—е®«ж–Үйҹ¬иҜҙиҝҷйҮҢжҳҜдёҖдёӘе№іиЎҢдё–з•ҢпјҢзңӢжқҘпјҢиҝҷе„ҝжҳҜд»Һе”җжң«е®ӢеҲқе№іиЎҢеҲҶејҖзҡ„еҸүпјҢиҝҷйҮҢиҜ»иҝҮд№Ұзҡ„дәәпјҢзҹҘйҒ“дёҖдәӣе”җиҜ—пјҢеҸҜеҚҙдёҚзҹҘйҒ“иҫӣејғз–ҫпјҢе°ұиҜҙжҳҺдәҶиҝҷдёҖзӮ№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ұӢйҮҢж— зәҝдҫӣз”өжҠҖжңҜеҲ°еә•жҳҜ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е„ҝе‘ўпјҹдёәд»Җд№Ҳ他们зҡ„иҙ§еёҒдёҚжҳҜйҮ‘银иҖҢжҳҜеҮӯз©әжҳҫзҺ°зҡ„иҷҡжӢҹиҙ§еёҒе‘ўпјҹ
ж”Ҝж№ғжӯЈеңЁиғЎзҗўзЈЁпјҢй»„йҰҶдё»е’ҢжқҸеӯҗйғҪд»ҘдёәжҳҜд»–еҚЎеЈідәҶпјҢй»„йҰҶдё»жү“е“Ҳе“Ҳз»ҷи§ЈеӣҙпјҡвҖңеӨ©иүІдёҚж—©е•ҰпјҢжқҸеӯҗиө¶зҙ§еҺ»зғӯй…’пјҢд»Ҡе„ҝжҷҡдёҠе°ұи®©иҝҷдҪҚе…¬еӯҗеңЁиҝҷе„ҝжӯҮжҒҜдәҶеҗ§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еӣһиҝҮзҘһж‘Ҷж‘ҶжүӢпјҢж·ұеҗёдёҖеҸЈж°”пјҢиЎҢдә‘жөҒж°ҙдёҖиҲ¬иҝһиғҢеҮәдәҶдёүеҚҒеӨҡеҸҘеёҰиҠұзҡ„иҜ—еҸҘпјҢдёҖеҸЈж°”е·®зӮ№жҶӢжӯ»гҖӮ
ж”Ҝж№ғзңӢзқҖзһ зӣ®з»“иҲҢзҡ„жқҸеӯҗпјҢиҜҙдәҶеҸҘпјҡвҖңеҗҚиҝҮе…¶е®һпјҢдёҚиҝҮеҰӮжӯӨпјҒжҲ‘жӣҫз»Ҹи®ӨиҜҶдёҖдҪҚиҠұжңҲ姑еЁҳпјҢйӮЈжүҚжҳҜиүІиүәеҸҢз»қгҖӮеҢ…еӯҗпјҢдҪ з»ҷдәә家жҸҗйһӢйғҪдёҚй…ҚпјҒе‘ҠиҫһпјҒвҖқ
й»„йҰҶдё»еңЁиә«еҗҺеұҒйў еұҒйў зҡ„и·ҹзқҖпјҢж”Ҝж№ғиҜҙйҒ“пјҡвҖңй»„йҰҶдё»пјҢдҪ дёҚеҝ…жӢ…еҝ§пјҢжҳҺеӨ©жҷҡдёҠжҲ‘дёҖеҮҶе„ҝжқҘпјҢдҪ еӨҡеҮҶеӨҮдёҖдәӣеЎ”еёғд№ҹе°ұжҳҜдәҶгҖӮвҖқ
й»„йҰҶдё»еҝғиҠұжҖ’ж”ҫпјҢеҝғйҮҢжғіпјҡвҖңе°ҸеӯҗпјҢеҲ«зңӢдҪ зҺ°еңЁзҢ–зӢӮпјҢеҸӘиҰҒдҪ иҝҳж•ўжқҘпјҢйӮЈдҪ е°ұеҫ—жҠҠиЈӨеӯҗйғҪиҫ“еңЁиҝҷе„ҝгҖӮвҖқ
дҪҶд»–еҳҙйҮҢеҚҙиҜҙпјҡвҖңжӮЁж”ҫеҝғпјҢиҝҷзҰҸиҝһеқҠжҲ‘еҸӘеҚ е°ҸиӮЎд»ҪпјҢеӨ§дёң家жҳҜжң¬йғЎйғЎдё»иөөеӨҸиөөеӨ§дәәпјҢжӮЁе°ұжҳҜиөўиө°дёҖдёҮдёӨдёҮпјҢйӮЈд№ҹиғҪз»ҷжӮЁеҮ‘йҪҗ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Ӯ№еӨҙпјҡвҖңйӮЈжҲ‘е°ұж”ҫеҝғдәҶгҖӮвҖқ
ж”Ҝж№ғзӮ№еӨҙпјҡвҖңйӮЈе°ұжҳҺе„ҝжҷҡдёҠеҶҚдјҡдәҶпјҢжҲ‘жңүдёҖдёӘиҰҒжұӮпјҢи®©еҲҡжүҚйӮЈдёӘеҢ…еӯҗеҒҡеә„пјҢжҲ‘иҰҒе’ҢеҘ№иөҢиүІеӯҗгҖӮвҖқ
вҖңжІЎй—®йўҳпјҢжҲ‘жқҘе®үжҺ’пјҢжӮЁж”ҫеҝғпјҢжӮЁж…ўиө°пјҒвҖқ
й»„йҰҶдё»жҠҠж”Ҝж№ғйҖҒеҮәдәҶжҘјй—ЁпјҢдәІиҮӘе®үжҺ’дәҶдёҖд№ҳжҡ–иҪҝпјҢзӣ®йҖҒж”Ҝж№ғзҰ»еҺ»гҖӮ
зӣёе…іжҺЁиҚҗ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иҮӘж•‘з»„з»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жң«дё–жұӮз”ҹ:жҲ‘иҰҒеҪ“еҘізҡҮ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јҖеӯҰи§үйҶ’еӨҡйЎ№жҠҖиғҪ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иҝҷдёӘдё§е°ёжңүзӮ№жҖ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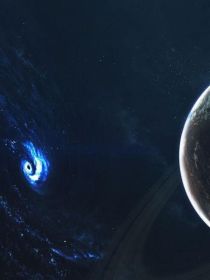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
еҪ’дәҺжҳҹе°ҳ
 иҝһиҪҪдёӯ
иҝһиҪҪдёӯ